
作者:周凌峰
在官修史书和民间话语两种有机关联又各有偏重的叙事体系中,南宋通常被视为北宋的附庸。因此,人们评论南宋高宗一朝史事,容易带上先入为主的标签,似乎这段长达数十年的历史,就是在“恢复”和“乞和”之间一路摇摆,两派的代表分别是岳飞与秦桧,至于真正起主导地位的宋高宗赵构,反而面目模糊,遁入了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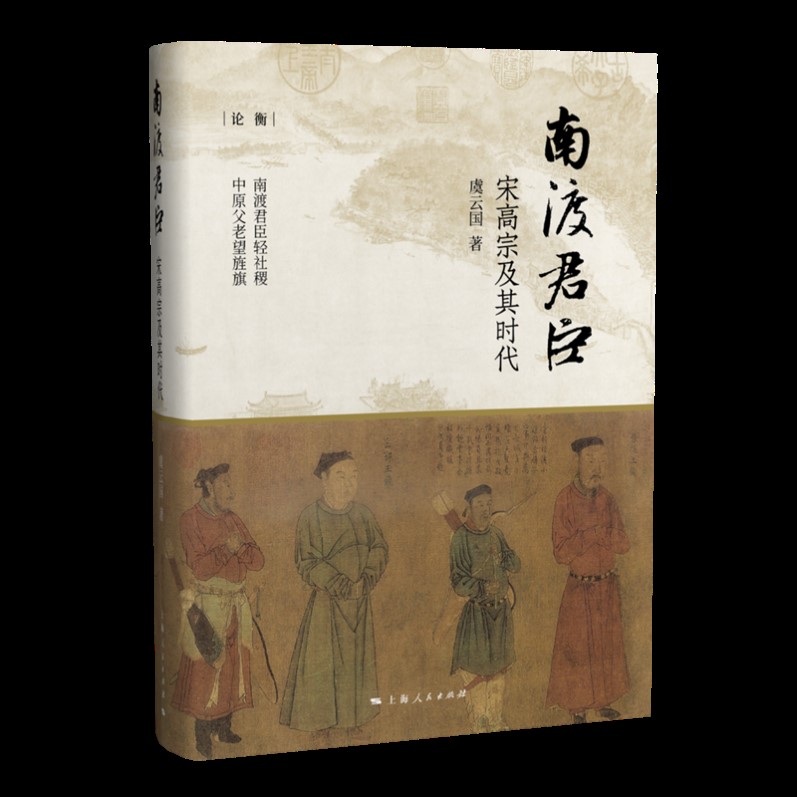
《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虞云国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8月第1版
虞云国教授《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以精准的史实和综理密微的分析,还原了宋高宗主导形成“绍兴体制”的全过程,在虞云国教授看来,这一君主与权相合谋以专权的模式,贯穿南宋始终,从而形成了南宋独特的政治格局:
纵观整个南宋政治史,绍兴体制确立的君主与权相结合的独裁格局,尽管在不同时段有强弱显隐之别,却几乎没有本质的变化。
在世人印象中,文彦博所说的“(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构成了宋代政治的底色,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活跃程度,堪称空前绝后,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宋代“祖宗之法”注重权力平衡,为士大夫参与政事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
有惩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先鉴,宋朝君主首先在制度上确立了中书门下治政事、枢密院治军事的二元体制,同时赋予台谏相对独立的监察权,因此有“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的说法,这些都保证了北宋前期至中期政治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以强势著称的神宗朝宰相王安石,在皇帝全力支持下展开变法,动作幅度再大,也未能撼动枢密院和台谏的地位,可见北宋帝王恪守家法之严。至于徽宗朝宰相蔡京,虽然深得帝心,不过附贰天子以狐假虎威,实际是称不上“权相”的。
假如我们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南宋,无疑会陷入被动。初入宋人的语境,往往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即任何政治上的改弦更张都要“循故事”而动。这样固然可以把握住历史脉络中存在的延续性,却容易忽视历史时间轴上产生的“基因突变”,毕竟任何历史事件的产生,都得基于具体情境下的“场”,惟其如此,才能理解当时人行事的路径,以及路径之外的权变。
高宗朝的政治模式与北宋有着明显区别,原因就在于南宋立国的情势迥异于北宋。
时间回到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东京,掳走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是为高宗。撇开宋高宗、光尧(赵构的尊号)这类称谓,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一年赵构才二十岁。尽管古人不乏少年老成的例子,但这位生于深宫之中的皇帝显然不在此例,他精于书法、文学造诣深厚,却没有受过像样的政务和军务训练。
高宗早年施政毫无章法,遇到金兵进攻只会逃跑,甚至在二十二岁时遭遇“苗刘之变”,被迫退位为太上皇。凡此种种,都可见高宗根本就没有做好“中兴”的准备,他只是比被掳去(宋人隐晦地称之为“出郊”)的兄弟们运气更好而已。
与其说高宗是在战乱后收拾旧山河,不如说他得把父兄散落的地盘一块块拼拢来。宋太祖创建北宋时统领禁兵已久,高宗却谈不上有什么嫡系,唯一拥有的就只有一顶皇帝帽子。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何在即位的第十二年明确转向求和,不但拔擢秦桧为宰相,还不惜改变祖宗成法,任命秦桧为“独相”。
虞云国教授在《南渡君臣》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秦桧任宰相后改变政治生态的关键举措:
秦桧专政最关键的招数就是“择人为台谏”,让原来兼具监察职能与议政职能的台谏官沦为其私人鹰犬,指东不西,成为他打击政敌、左右舆论的忠实工具。
如此一来,监察大权纳入相权之内,北宋视为国之元气的台谏失去了原有的制衡功能。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也可窥见秦桧揽权的力度:绍兴元年和绍兴八年,秦桧两次入相,均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这意味着北宋政事和军事分开的原则也被完全打破,这是对前朝制度的一次重大颠覆。
宋高宗之所以如此施为,仍然与当时的情势有着直接关联,虞云国教授指出,南渡诸将帅几乎都有扩军自雄的情况,武将政治地位陡然上升,甚至自选将佐僚属,移罢州县长吏。这与北宋时期崇文贬武的情况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宋高宗在局势基本稳定之后,效仿乃祖“杯酒释兵权”,更以莫须有的理由杀害岳飞,以宰相兼领枢密院,都是对这一现实情况作出的反应,宋高宗的着眼点始终只有一个:巩固自身权力。囿于北宋以来固有的政治模式,他无法另外建构一套新体制,唯有不断加强代理人秦桧的权限,变相集权。
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原本也没什么不可以,但制度上的改变一旦形成惯性,产生的后果就很难预计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之后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都走上了这条专权路子,算上秦桧,这四大权相合计垄断朝政七十余年,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高宗立朝时的非常之策,就这样成为南宋无法剥离的“路径依赖”。
《南渡君臣》的书名,来自赵孟頫诗句“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赵孟頫以宗室之后,对于家国沦陷自有刻骨感受,宋人著述中也不乏“南望王师又一年”的集体记忆,可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不得不做别的打算。以著名道教宗师王重阳为例,关中失陷,他只能去金王朝扶持的刘豫政权应试,之后又中了金朝的武举,掐指算来,此时离北宋灭亡也不过十余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