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阅读提示】
《我的天地国亲师》是李零先生的一部忆旧集,汇集了他近30年所写的怀念亲友、师长,以及记述自己人生经历的文章。作者笔下的天地国亲师恰似一面面镜子,投射出彼此的人格和人性。我所感兴趣的是李零先生杂忆间出其不意的种种新“发现”。尤其是关于父母的杂忆,于作者而言是人之子对“咱妈咱爸”历史底色的白描;对读者而言则可通过两份个体微观史案例,引发有关妇女解放、启蒙、革命等相关话题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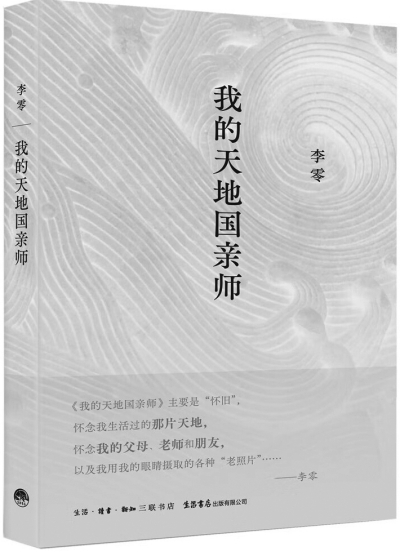

《我的天地国亲师》,一个天长地久的话题。当它们出自历史学家李零笔下,你会读出常谈常新的惊喜。作者所谓“天地国亲师”,主要是由父母老师亲友所构成的凡人世界。作者仿佛漫步于岁月陇上,持一份平和平视的姿态,触摸人性感悟常道;大道至简如话家常的叙事修辞,自觉与学术腔的高谈阔论保持距离。可谓微笑热泪在脸上闪烁,清幽冲淡在笔下流淌。活生生的人性,鲜活的人间生活,那底色正是作者心目中的历史本色。那些微观的个人,虽不能左右历史进程,却构成了历史的鲜活血肉。
李零先生自称“我是野生动物,长期在野外生存。我是学术乞丐,吃百家饭长大”。考古专业出身的他,下笔自带考古专业的现场感、野外生存的鲜活感、“学术乞丐”的百家感、晋地京畿的乡土感、即兴插入的当下感,可谓“百感”交集。作者又说自己的文章是“杂文”。借用黄子平的说法,“所谓杂文,我想,无非是在看似没有矛盾的地方出其不意地发现矛盾,而这‘发现’带有文化的和文学的意味罢了”。我所感兴趣的正是李零先生杂忆间出其不意的种种新“发现”。尤其是关于父母的杂忆,于作者而言是人之子对“咱妈咱爸”历史底色的白描;对读者而言则可通过两份个体微观史案例,引发有关妇女解放、启蒙、革命等相关话题的思考。
“咱妈”故事:从出走到回归
惜墨如金的李零先生,专写母亲的文字有两篇:《大山中的妇女解放》和《母也天只》。两篇都很短,却有“三言两语提炼千言万语”的功效,细思之下,颇有“文化的和文学的意味”。毫无疑问,母亲是他关注女性、发现女性的起点。《大山中的妇女解放》是一个旧时代农村妇女离家出走闹革命的故事,在中国现代史上并不少见。我读李零母亲的版本,关注点聚焦于“出走”动因和“回归”成因。母亲出走的动力源于女性之间的压迫:婆媳仇恨。母亲1908年出生在晋东南小山村,嫁到相距七八里的另一个山村,因为迟迟不能怀孕,被家里的女人——婆婆恶毒咒骂,一日三餐遭歧视,让母亲成了“最恨她婆婆”的儿媳。身为儿子的李零从母亲的切肤之痛中发现,“妇女受歧视,那是全方位的,不光被男人歧视,也被女人歧视,更多是被女人歧视。”无独有偶,赵树理的小说中也有不少这类书写。《登记》里小飞蛾的婆婆“教育”儿子要狠狠打媳妇,打几次就老实了。因为她自己年轻时候也是这么被打过来的。《传家宝》中金桂的婆婆、《孟祥英翻身》里面孟祥英的婆婆,都是压迫媳妇的高手,都用从自己婆婆手里接过的“传家宝”传递歧视,践行同性压迫。为什么?李零先生一针见血指出:“婆婆是女性,但代表的是男性,代表男性的传宗接代。千百年来,男性的歧视是靠女性传递。可怜媳妇熬成婆,又拿媳妇来出气。”李零经由母亲“揭秘”坐实的这个现实版,颠覆了我们在性别文化结构中形成的刻板印象:那就是,在歧视压迫女性的阵营中,来自“同一战壕”的自相残害教训沉痛不可小觑。不过,幸运的是,她的革命丈夫给了她启蒙,帮她完成出走,参加革命。母亲成了1930年代为数不多从晋东南大山里走出的革命妇女。始料未及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剧情出现了拐点:离开婆婆的压迫走上革命道路,又遭遇了启蒙者丈夫的另一种“歧视”。战争年代领导让她当县长,丈夫却拦住说,你就好好在家带孩子吧;随解放大军进京,赶上和平年代的干部评级,丈夫又说,你没文化,级别就该定很低。于是,“她一辈子都在生我爸的气,一辈子都与我爸作对。”理由不言而喻:曾经的启蒙者丈夫翻脸成了把妻子拖回家的“推手”。
出走又复回归,妇女解放何处是归程?放眼中国现代妇女的解放,多是从城市家庭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觉醒开始。但“怎么看怎么像农村妇女”,“手巧,但一辈子干活,手很粗糙,关节肿胀,好像鸡爪”,“一辈子最恨男女不平等”,爱唱《妇女自由歌》,对自己的孩子永远带着“乡土气息的动物式的爱”的“我母亲”,算不算彻底解放的妇女呢?李零先生坦言自己是“母党”,饱含对母亲的同情理解,直指无法回避的“已解放的妇女的双重角色的矛盾”。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近现代史上,是男性知识精英率先呼吁鼓吹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甚至引领女性参加革命。岂不知像“我父亲”这样的男性,身为革命队伍中的先进分子,在社会上理所当然倡导妇女解放,转身回到自己家中,面对自己的妻子,却持双重标准。进步革命家庭的女性真实的现实处境和苦楚,很遗憾却被长期遮蔽。身处具体社会关系中的“这一个”女性不尽相同的人生,算得上李零的一项“考古”新发现。你会吃惊于历史的复杂性和无限可能性:封建家庭的女性家长和革命家庭的男性家长作为“同构性的人”,在妇女解放的辛苦路上,扮演过不同程度的“绊脚石”。我们不得不回到那句经典老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咱爸”故事:“这一个”少年先锋
“这一个”是借用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的典型形象术语,用来指称“我父亲”个体生命经历的不可替代性。父亲的故事放在大历史当中或许微不足道,放在私人史里面却足够传奇。他早年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却没有背叛包办婚姻的乡下妻子,还带她离家出走闹革命;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死里逃生回乡组织青少年革命,1929年被同窗作为原型塑造为小说《少年先锋》的主人公。他还是一位参加过狂飙社文学活动、发表过小说的“文士”,毫无疑问接受过进步思想的影响,深谙妇女人格独立、男女平等的历史现实意义。他带妻子离家参加抗战的壮举,堪称男性精英对女性的一次“人的发现”,让大山深处受压迫的妇女获得了解放。吊诡的是,在随后的革命路上,他却屡屡断了妻子追求进步的念想,夫妻俩在吵吵闹闹中度过一生。回溯“我父亲”的人生历程,年轻时曾和自己的封建父亲对立对骂,晚年又到父亲坟前号啕大哭;打过二十多年仗最后讨厌战争,当过二十多年领导最后腻味做官;和平时期痴迷古史和老家沁州方言,幻想做一名学者,最终一事无成。李零对父亲前世今生的审视,好比边缘缝隙的考古,发掘个体被忽视被压抑的无意识,“可能比小说、诗、戏剧等文体更贴近历史文化主体及其精神世界的真实”。父亲充满矛盾悖论的人生,母亲一辈子的委屈不甘,父母吵吵闹闹的一生,竟然是殊途同归的“出走/回归”式轮回。这方水土中的父子母子、婆媳夫妻,剪不断理还乱,却又藏着驳杂难言的历史隐秘。
风格即人格
回到常说常新的老话题:风格即人格。作者笔下的天地国亲师恰似一面面镜子,不但投射出彼此的人格和人性,也让我们对“这一个”历史学家的出生家庭、学术生涯、文风人品有了真切的了解体味。该书谈天说地臧否人物,本色简色与趣味情味交相辉映,属于文体不拘一格的有趣文本。比如他的“呀”字句。作者笔下重情却吝于抒情。情不自禁的时候,“呀”的一声,戛然而止。原始记录稿怎么也找不到了,“真可惜呀”;邵循正先生“人真好呀”;社科院的前辈“都是了不起的人呀”,等等。他说过,“‘字’是在语境下被释读,”,“字不是孤立的东西”。我吃不准李零先生这个语气词的语境,但是,李先生的“呀”字句绝不轻飘孤立,大有表现力。
李零先生谈人论事秉持超越立场的立场,钟情乡土而不拘于习俗偏见,爱父母而不囿于为尊者讳,论及师友的学术批评心怀敬意,朴素中见公允,常理中含新知,举重若轻春秋笔法,读人度己文不猥琐,颇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大家视野。李零的杂忆是建立在自己的语言学和史学理念之上的一种娴熟叙事,比起尊崇理论,他更相信生活中的感受和理解。他用简约的白话写出真人真事背后的历史性质,恬淡冲虚间迸发的火花,哪怕只是一小点,却不会归于落寞,而是激起悠长的回味。在我看来,《我的天地国亲师》作为个体微观史的魅力就在于此。
(作者郭剑卿为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