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赵天成
在《时间缝心》的开篇,作者写道:“这世间不能没有国王先生,他就是美本身——这种美不只是形体面庞这样肤浅的美,而是从灵魂深处渗透出来的美感——他无时无刻不在美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王先生竟渐渐代替了我热爱的艺术。不论艺术是多么被世人称颂,多么伟大,多么抽象,在我的心里,他的名字,就等同于艺术。”
如果故事这样发展下去,“我”的国王先生,会成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是爱、美、神的中介,崇高之物的世俗显像。更有可能的是,小说中会生成勒内·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所说的“欲望三角”,主体、客体和介体三者构成小说的能量场。国王先生是欲望的介体,“我”之爱国王先生,是爱艺术,或者艺术的社会化以及由此折射的幽微人性。这样,“我”会进入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的序列,她们斩断现世安稳的根基,自觉不自觉地引火上身,迎向强烈、灼热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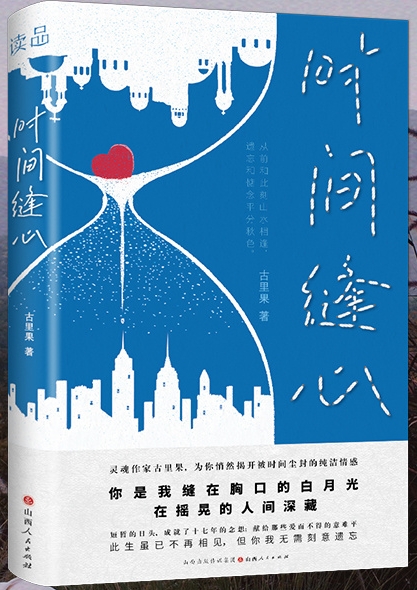
女性主体的成长
但显然,《时间缝心》的主人公,不是基拉尔所谓的“虚荣人”——她对嫉妒、攀附和外部世界毫无兴趣,也不需要向他者挪借欲望。尽管小说主要的人物关系,也可以概之为三角(△)——叙述人“我”为中心,国王和哥哥分居两侧,但主人公的欲望始终是直线式的,由主体直达客体。只是由于时间和引力的变化,线条弯曲时而或成弧。虽然欲望曲线的延伸,是小说贯穿性的线索,但“我”始终是不想走出家门的娜拉,只是因为“缘分”的意外闯入,心间出现了一道裂缝,留待时间的修补。
是的,时间。如果恰如书名,小说就是一个“时间缝心”的故事——时间是缝补内心的裁缝和医生,那么在主题学的意义上,它可以归为女性主体的成长:是成长史和编年史,也是回忆录和忏悔录。但《时间缝心》所提出的,实际是时间体验的难题。即使不说女主人公拒绝成长,她的成长也是向内生长,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精神活动。
沉浸式书写
通常成长小说常见的内外联动——即以内心生活映射社会生活,进而自我与社会(自我体验中的社会)一同成长,在这部小说中几无影踪。在这个意义上,《时间缝心》是罕有的,不带任何时间性和外部性的女性成长故事。我将这种写作形式,称作沉浸式书写——主人公、作者,及作者期待中的阅读体验,都是深度沉浸式的。显而易见的是,女主人公浸润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小楼一统,无论春秋。而作者跟主人公做了同一件事,完全沉浸身到心灵,沉浸到感觉和情绪中。她在自己的讲述中沉醉,就像主人公在爱琴海、韩国烟、Realm红酒、画室的炉火和幻想中沉醉。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沉醉者总是时间的不感症者,他们的时间体验,与醒觉者决然不同。从大学毕业至人到中年,在女主人公的心理感觉中,实是十年如同一日,即使以友人满含善意的目光打量,也是如此:“恩禾是个聪慧体贴的女孩子,她知晓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读了四年大学,却没上过一天班,这有些不可思议。他人眼中的幸福生活,也许,在某些人看来,只是毫无价值的虚度时光。”
女主人公以“月亮”和“太阳”,分别喻指填满她十余年人生的两个男人。而在恩禾等旁观者看来,她的十年一觉,不过是日东月西,是一夕之间可以完成的选择;她的心灵的转变,或者说缝合——即抵达小说末句“月色很美,可月光很冷;而太阳,永远是热的”的认识,并非来自时间累积的理性经验,而是带有神秘力量的“突转”和“发现”。“突转”对于月亮(国王先生),“发现”对于太阳(哥哥)。“突转”是痊愈,是情感高烧的平息,精神官能症的纾解;“发现”则源于疾病,“直到窥见他将要转身的背影,我终于在剧痛和大病中明白了,我在爱他”。疾病的隐喻性转换,意味着客体——主体投射对象的变化。然而这是欲望曲线的变换,而不是欲望模式的变换。
近乎非虚构的粗粝质感
古里果素以文笔华丽著称,但《时间缝心》最引人注意的文字风貌,是字里行间偶尔显露的,近乎非虚构的粗粝质感。特殊的主观时间体验,涂改了常规时间的深度与厚度模式,一天、一年、十年、二十年,物理时间的跨度不再是由此及彼的桥梁,而是一面略有弧度的镜子,镜中是“我”曾经的样子。
文论史的语境中,以自我的形象为轴心,沟通诗与画、作家与画家,乃至将文学写作比之于自画像,产生过诸多富有启发的讨论。在美术领域,伦勃朗的自画像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西美尔在《伦勃朗:一篇艺术哲学论文》中分析说:“提香、撒托、查万尼和波克林都留下了一些自画像,在其中他们试图一劳永逸地捕捉住自己不变的特质。但是,在伦勃朗的自画像中,正如整个生活流入那如同一幅图画那样呈现的每一时刻,它也进一步流入下一幅绘画……它永远不是所是,而总是生成。”在文学(尤其是小说)的意义上,现代读者更能欣赏镜中自我的参差多态,就像道连·格雷那般,美少年容颜不改,承受其罪恶的画像日日变得丑陋。当道连终于不堪忍受,挥剑砍向画像之时,他的面容瞬间苍老,画像却崭新如初。自我与画像(镜像)的背道而驰,隐含的正是艺术的本质性问题,即自我与人物、文学与生活、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隔问题。在生活的世界里,倾诉与剖白是勇敢的;在小说的世界里,倾诉与剖白也是勇敢的,但是嘲讽与奚落,或许更为勇敢。众所周知,福楼拜一方面声称“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另一方面又自诩是第一个有能力取笑他的男女主人公的小说家。
朗西埃在《为什么一定要杀掉艾玛·包法利》中,细致探讨了福楼拜和其他小说家,是如何与其人物划清界限的。经由这种界限,小说家可以让人物精神分裂,自己却能审判、杀死抑或治疗他的人物,从而让自己保持健康,让文学保持健康。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朗西埃借弗吉尼亚·伍尔夫《海浪》中的人物罗达,提出了一种写作者的疗愈模式:“从‘个人的存在的疯狂’中逃离,让自己的认知范围越来越广,直到容纳整个世界。她幻想‘我们可以吹一个特别大的气泡,大到够太阳在里边升起落下;我们可以把蓝色的白昼和漆黑的午夜一起偷到手里,然后马上就从这逃走’。罗达的想象正是福楼拜笔下的魔鬼让圣安东尼去做的:打破主体性对自身的限制,投身于客观生活的此间中。”
古里果吹起了一个泡泡,这个泡泡还可以更大——只要她愿意考虑,杀死自己的主人公,杀死镜子中昨天的我。因为归根结底,《时间缝心》及其所关乎的,是女性个体如何与自己的命运相遇,继而在风暴退去之后,生成一个崭新的自我。(赵天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