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谷海慧
大概没有一位戏剧编剧,能像美国当代剧作家山姆·谢泼德这样传奇。他集演员、导演、剧作家、作家、摇滚乐手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并在各个领域都令人瞩目。作为一生创作了五十五部戏剧的天才剧作家,他拿下了包括普利策奖在内的十多个奖项,被《纽约客》杂志称为“他那一代的伟大美国剧作家”。南京大学出版社今年8月出版、孙冬翻译的《被埋葬的孩子:山姆·谢泼德剧作集》,收入了他创作于1977年至1980年间的《饥饿阶级的诅咒》《被埋葬的孩子》《真正的西部》等“家庭三部曲”,集中展示了谢泼德在破碎的家庭、孤绝的个体、神秘的诗意上的伟大创造。

剧作家山姆·谢泼德(1943-2017)
破碎的家庭:我不能永远待在这里
“家庭三部曲”不妨被叫作“破碎家庭三部曲”。因为这三部作品呈现的家庭关系都是破碎、扭曲而又危险的。同床异梦的夫妻、彼此排斥的父子、互不理解的母女、自相残杀的兄弟……在一个个危机四伏的家庭里,充满暴力和死亡阴影。正因为如此,“我不能永远待在这里”成为三部剧作交叠的声音。《饥饿阶级的诅咒》里,它是多人使用、多次复现的台词;《被埋葬的孩子》中,它是从哈莉背叛到儿孙试图远走的三代人都有过的尝试;《真正的西部》里,它是弟弟奥斯汀想跟着哥哥李去沙漠流浪的表达。显然,逃离与出走是三部作品的共同主题。然而,在这三部层次丰富的作品中,与之并行的,还有另一个完全相反的主题——回归与留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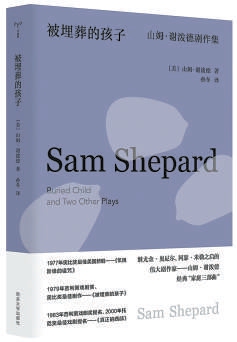
《被埋葬的孩子:山姆·谢泼德剧作集》
三部作品中的家庭虽暗黑,却不乏温情与暖意。这让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变得复杂,羁绊了那些想要出走者的脚步。我们看到,《饥饿阶级的诅咒》开场时,女主人埃拉和她的丈夫韦斯顿各自做着卖掉房产、远走高飞的打算,一儿一女也都想离开这个家。然而,没过多久,儿子便生出“修整”房子,亦即家庭的愿望。因此,当父亲离家踏上复仇之路后,穿上父亲衣服的儿子便成了新一代的家庭维护者。《被埋葬的孩子》里,已经离家六年的孙子文斯本来只是回来看看的过客,最终却成为留下来代替爷爷道奇的主人,以跟爷爷同样的姿态盘踞在沙发上,形神毕肖地成为爷爷的变体。《真正的西部》中,哥哥有对“天堂”一样的家庭的向往,弟弟数次表达对哥哥的情意,兄弟二人都对妈妈的家充满了热爱与依恋,残酷的决斗似乎只是一个激情事件。
这些暗黑的家庭在破碎之后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下一代的回归和留守延续下来。一种不知名的来自血液的内部力量,让上一代“附体”于下一代,让每一个“家”都有自己的血脉宿命。由此,逃离与留守这两个反向主题构成了巨大的戏剧张力。
孤绝的个体:你们看到我了吗?
破碎的家庭缺乏健康的关系,也很难长出健全、完善的人。“家庭三部曲”里,活动着一堆“活死人”。他们精神恍惚、行为怪异,打着各自的算盘,怀揣大小秘密。
虽然以“家”的名义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极为艰难。孤绝是他们的共同处境。《被埋葬的孩子》开场,哈莉与道奇的“对话”隔空展开。楼上的哈莉絮絮叨叨地冲道奇喊话,道奇给予的只是文不对题的回应。哈莉捕捉不到任何信息,“什么?”“什么?”的不断追问,显示出两人间错位的不仅仅是空间关系。同时,相互否定也让交流更为无效。譬如关于赛马,两人的记忆截然相反,各自斩钉截铁的坚持让交流成为一场否定和拆解。因此,从严格意义上看,他们并没有构成对话。同样,《真正的西部》开场时,人物间的交流也迟迟没有推动情节进展。这类无效信息的有效性,就在于显示自说自话是一种常态。
孤绝的个体总是处于被误解、被忽略、被无视中。无论完全认不出孙子的爷爷,还是将儿子当成丈夫的母亲,长久或暂时的失忆封堵了交流的可能。作为外来者的雪莉,深切感到道奇家每个人都对她充满漠视甚至敌意。“我在呼吸。我在说话。我还活着!我存在着。你们看到我了吗?”她彰显自己存在的急切愤怒的表白,代表了谢泼德笔下每个人物的心声。然而,虽然每个人都热切渴望被听到、被看到,害怕孤独和失群,但他们只会以自欺安慰自己,以置身事外的冷漠对待他人。并不存在的安塞尔,被哈莉想象成一个英雄;虽然冰箱空空如也,埃拉坚决不承认他们家属于饥饿阶级;李渴求体面生活,奥斯汀则虚拟流浪沙漠。他们都是想象的狂徒和行动的奴仆,对被关爱的极度渴望与极度缺乏让他们越发孤绝和畸形。
神秘的诗意:你不能干涉它们的生长
“家庭三部曲”既残酷又诗意。哈莉面对那些从未被种植却蓬勃生长的玉米说:你不能干涉它们的生长。万物自由生长,宿命难以抗拒,神秘的诗意就产生于此。这些家庭的隐秘和人物的样貌固然离谱,但在前因后果中又合乎逻辑。通过半遮半掩的叙事、有意味的意象符号以及富于想象性的开放式结尾,神秘的诗意自由流淌在谢泼德剧作中。
在欲言又止的对话中,每个故事仿佛都暗藏阴谋,使得“家”这个理应最安全的地方充满危险和恐怖。《被埋葬的孩子》中,父子、夫妻的对话时时暗示这个家里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直到作品接近尾声,那个被埋葬的婴儿的秘密方被揭开;《饥饿阶级的诅咒》里,妻子和丈夫各怀鬼胎,却各自被骗,卖房产和被骗的秘密在尾声时合二为一;《真正的西部》里,制作方改变主意的原因则是一个真假难辨的问题。而在揭秘过程中,无处不在的危险气息总是令人不安。谢泼德通过大量的细节化舞台提示不断强化这种危险气息。他的舞台提示极完整,涉及神态、动作、声音、气味,以剧作家强势介入的姿态完成激发读者想象力的诗意写作。
增加谢泼德作品诗意的神秘的,还有每部作品中的意象符号。被破坏又被修复的门、通向外面世界的烈马或汽车、直接作为道具或不断被提及的刀和枪、被牵上舞台又被牵走杀掉的病羊、被碾碎又被大口咀嚼的吐司、越来越急促而疯狂的郊狼的嚎叫,都充满了神秘不可测的力量,在隐喻和象征意义上,帮助读者破解真相与谎言、暴力与温情、愿景与现实之间的秘密。
尤其令“家庭三部曲”富于诗意的神秘的,是这三部作品的结尾。《被埋葬的孩子》收束于埋葬婴儿的后院长出辉煌玉米的奇迹;《真正的西部》结尾定格在势必你死我活的兄弟的对峙;《饥饿阶级的诅咒》结尾那个故事中的故事,暗示韦利埃为保护他的“羊卵”——家,而要像山猫一样与欺压他的“老鹰”同归于尽。这些残酷但合理的结局,让探险式阅读止于无限开放的宁静与沉思,延长了谢泼德剧作诗意的神秘。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原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