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刘进宝
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西行,通过甘肃河西走廊和今天的新疆(西域)地区,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伊朗等地,连接亚洲、欧洲的交流和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在我国境内所通过的地区,主要是陕西、甘肃、新疆、青海等省区。《西北史地与丝路文明》就是将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与所经过的重要地区——西北紧密结合,探讨其间的关系。

张掖平山湖大峡谷 杨 潇
本书首先将西北史地和丝绸之路置于“东方学”的视野下进行讨论,而“东方学”是一门以研究东方历史、地理、民族、文化为重点的学科群,它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作为治学的主要方法。“西北史地学”是面对西北边疆的危机,我国学者“经世致用”,自发地从事有关问题的研究。东方学与西北史地学兴起的时间和学科的特点相近,研究的方法也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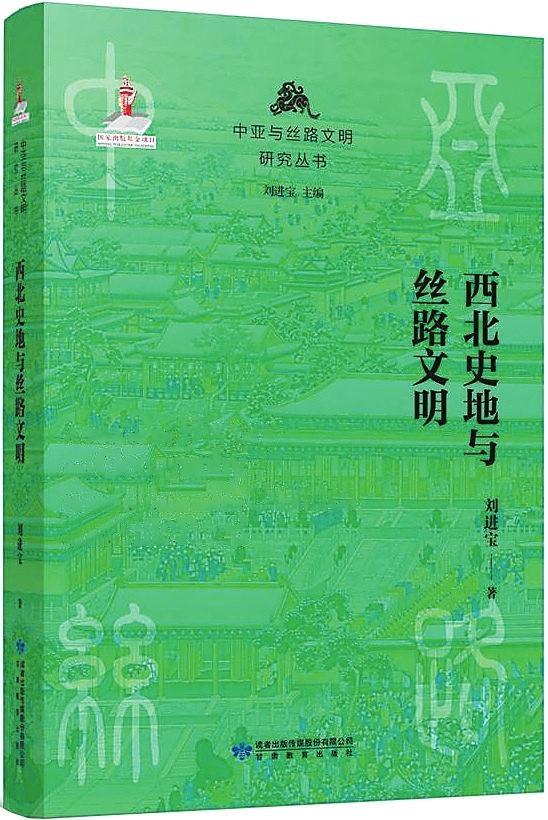
(《西北史地与丝路文明》,刘进宝著,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丝绸之路”则是在近代中亚探险的背景下由西方学者提出的。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在中国的考察共七次,他的考察既有学术的目的,同时还有为列强提供情报,便利其经济扩张的目的。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回国后,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中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
李希霍芬到中国考察时,并没有到达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他对丝绸之路线路的了解,主要来自文本而非亲身经历。他并没有研究中亚史地,“丝绸之路”一词也是他偶然、无意间提及的,所指也仅仅是从中国长安到中亚之间的东西交通路线,并将其理解为一条基本上笔直的道路。在《中国》第一卷中所附的“中亚地图”,历来被认为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线路图,其所描画的“丝绸之路”,基本上是一条直线。这并不是实际的“丝绸之路”,而是他心目中的“丝绸之路”、他想象的“丝绸之路”。其目的是按这条线路修建铁路,方便将新疆的煤炭运出去。
虽然“丝绸之路”是在西方对东方侵略的背景下提出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出现的背景而否认其科学性。因为“丝绸之路”的提出或“丝路学”研究,与东方学一样,都有其科学价值。
本书在宏观研究的同时,还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微观探讨,如《史记·大宛列传》中的“西城”和“西域”,丝绸之路的交流功能——双向共赢,丝绸之路的交流特征——转输贸易等,尤其是用较多篇幅辨析了“丝绸之路”一词在我国的传播和使用。虽然“丝绸之路”在1877年就出现了,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主要使用“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等名称。1933年9月,《北辰》发表的文章中,将张骞开通的中西交通路线称为“绸缎之路”。1935年,朱杰勤使用了“丝路”一词,可以看作是“丝绸之路”的简称。随后,国内出现了“丝道”“贩丝之道”“运丝大路”“丝绸路”等称呼,显然是指“丝绸之路”。1943年2月24日,《申报》在讲述16世纪葡萄牙对印度和马六甲的占领时,使用了“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这是目前我国媒体最早使用“丝绸之路”一词,从报道的全文可知,“丝绸之路”就是指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则是指海上丝绸之路。
虽然“丝绸之路”一词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已在国内出现,但使用的频率很低。“丝绸之路”一词较多地使用,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间的对外友好交往中。
在政府间的交往中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后,史学界也开始关注“丝绸之路”,如1966年第3期《历史教学》发表的《中国和非洲人民的历史友谊》中就使用了“丝绸之路”。史学界较多使用“丝绸之路”,则是新疆文物考古、历史研究工作者和研究新疆历史文物的学者,如1979年出版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2册、朱绍侯主编的十院校教材《中国古代史》、南开大学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教材,都出现了“丝绸之路”的表述。此后,“丝绸之路”的使用逐渐频繁,并出版、发表了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和论文。
本书除了探讨“丝绸之路”的出现及使用时间、范围外,还对所谓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定义进行了辨析。国内学术界在谈到李希霍芬关于“丝绸之路”的定义时,都说李希霍芬将“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并注明是引自李希霍芬的《中国》第一卷第454页。实际上,真正奠定“丝绸之路”学术地位的是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他在1936年出版的《丝绸之路》一书中,对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作了全面解题和阐述,并将其引入国际学术界。
目前,有关“丝绸之路”的名称比较多,其概念甚至有些泛化,但不论是按交通路线划分的“绿洲道”“草原道”“沙漠道”“南海道”等,还是以交换物品分类的“玉石之路”“青铜之路”“香料之路”“皮毛之路”等,这些扩大或充实了的“丝绸之路”,都是借用或参照了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概念。如果不加特别说明,当我们说到“丝绸之路”时都应有具体的含义,即从我国长安出发,经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到中亚、欧洲、非洲的古代交通道路。(刘进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