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冷 阳
捧读米正英(笔名蓝莲花)的新作《风从长安来》,发现这是一部诗画合璧的作品,它不仅是长安雄浑古风与江南湿润水汽的交响,更是一部以寂静禅心映照生命的精神史诗——在四辑长卷的徐徐展开中,完成了对双重乡愁的超越性救赎,抵达了万物有灵的澄明之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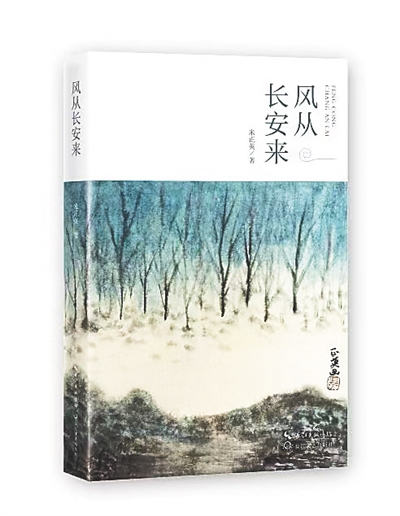
长安在米正英笔下绝非地理坐标,而是华夏文明的精神母体,更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在《风从长安来》首辑诗歌中,即以恢宏气象唤醒集体记忆:“谁牵起一条闪亮的丝绸/谁在松开时间的缰绳”,丝绸与奔马的意象将盛唐气象熔铸为动态的文化基因。当诗人谛听“隔世的琴音”,捕捉“看不见的绝唱”,长安已升华为永恒的精神灯塔,指引着穿越“漫长而苍茫”的存在迷途。
这种文明乡愁在《故乡,像一本忧伤的诗集》中化作草木含情的微观叙事:“井边柳/园中葵,霞光褪尽的云朵/随风摆动,不肯逝去。”诗人赋予自然物象以灵性生命,使其成为乡愁的永恒证人。而在《没有父亲的田野一片空旷》中,“不悲不喜”观照达到了极致,静默的枣树与空旷的田野,构成禅宗般的意境,将个人悲痛消解于宇宙的永恒循环。
米正英长期工作生活在江南镇江。江南的风物,江南的书写,显露出浓重的禅意哲思。《水意江南》中“雨一下就是一季”的黏稠时空里,诗人以“雨打芭蕉的夜晚/思乡的梦/总是歪歪仄仄”的妙悟,将乡愁升华为对无常的体认。这种超越性在《习惯》中臻于化境——诗人安然接受花开花落、瓜熟蒂落的自然法则,唯对“不发出声响”的铁皮桶心生涟漪。物我界限的模糊与对“无声之声”的敏感,正是禅心觉醒的征兆。
面对生命中无法弥合的创口,米正英的救赎之道是回归自然的怀抱。《种豆记》呈现了堪称典范的诗意疗愈:母亲去世后,诗人将悲怆转化为“种植红豆”的仪式。当她在菜畦边“倾听红豆拔节的声音,开花的声音”,这专注的聆听已然接近禅修的当下觉知。红豆从具体作物升华为“不朽的生物”,完成了个体创伤向永恒生命的诗意转化。
《樱花落》则将这种慈悲推向极致。诗人蹲身触摸落樱“扑向泥土时最后的颤抖”,是一种以肉身丈量生死的壮举。而《一条河》的干涸河床埋葬了双亲,但心中的诗之河永不枯竭——这恰是诗歌救赎的本质:以语言重构消逝之物,让痛苦结晶为超越时间的精神琥珀。
米正英的诗艺才情,因禅心浸润而获得神性维度。诗画同源的特性,在第四辑绽放异彩。《绘画记》中“精雕细琢,同归于寂”的创作状态,正是“制心一处”的写照。
最近十五年,米正英的诗歌完成了从才情迸发到“静水深流”的蜕变。《内心的声音》中“灌满了涛声”却保持沉默的深海意象,正是其艺术成熟的隐喻。
当《短章》中“这个夜晚何其美啊”,笔尖“沙沙作响”地游走宣纸,心“带着雪花一样的翅膀”飞越墨香原野,我们见证了一个诗人以禅心统摄万物的奇迹。
《风从长安来》最终超越了地理乡愁与生命创伤,构筑起“天地与我并生”的精神宇宙。那些长安的砖瓦、江南的雨丝、墓园的葵花、画纸的飞白,恰似诗句“我想对你说的话/已深埋,深到/黑暗无法照彻的/黄金”。都在诗性观照中焕发出光——这恰是米正英赠予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礼物:在洞见万物无常后,依然以悲悯之心、山水之心,为世界供奉一首“沙沙作响”的寂静之诗。(冷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