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范小青
《江山故宅》的写作,是一次“在场”的行走和行走的展示,因为“在场”,写作过程是畅快淋漓的,得意时自己都忍不住“咯咯”乱笑,难过时会热泪盈眶,这在我的曾经被认为是情感“零度介入”的写作旅程中,确实并不多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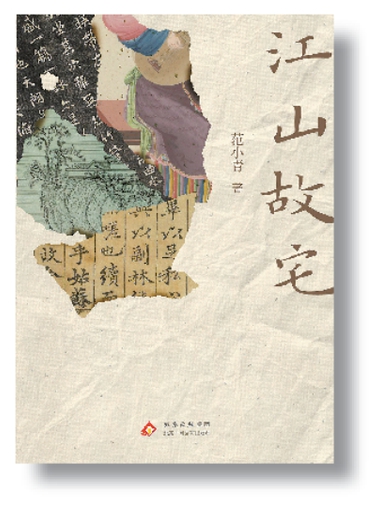
这里的“在场”,并不是单为这一部作品所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苏州和苏州的历史以及苏州的今天和未来,我始终是愿意“在场”,并且尽可能“在场”的。
所以《江山故宅》并不是一次或某一段时间“在场”的产物,它是许多年“在场”的积累,从我的写作初期走到今天的。
只是因为,今天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写作自然也会变化的。
首先,“在场”与屏幕里的“场”。在被网络覆盖的世界里,在时时处处都隔着屏幕的日子里,手机屏,电脑屏,大脑屏,毛茸茸的生活质感似乎已经成为稀缺之物——但其实,那个生活仍然在,始终在,就在你这里。
《江山故宅》在形式上是用心结构的,很刻意地造了迷宫,使得小说本身有一种设计感和工程感。
但是,要让读者,或者至少是作者自己,在迷宫中行走的路上,可触可摸可感,看得到风景,看得到人,看得到历史和现实的纠缠,甚至还看到有意外的惊喜,看到未曾想到的东西。
小说中交代的《春日家宴图》,画的是不易堂建成后言氏在家中举办家宴,展示出言氏大宅作为“第一豪宅”的全景,但是小说的最后部分却有这样的描写:
“我说,言子谌,也许从来就没有传说中以及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春日家宴图》。言子谌将杯中的咖啡一口喝完,站起身,说,走吧,我们去看看。
是的,我在‘故事’美术馆的一面墙上,看到了那幅《春日家宴图》,是一幅静物画,画面上是一些春天的蔬菜和少量的荤菜。这是言子谌从老罗林美那里带回来的,交给了他的红粉知己叶小姐。它确实就是《春日家宴图》。但是你们认为我会相信吗?
除了我,还有言子谌,他会相信吗?
还有许多人,他们会相信吗?”
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这图,却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图。
结果未必是有真相的,但是因为在迷宫中看到了许多,想到了许多,尽可能让人在读了“设计的过程后坦然接受其不完成性”,其实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重在过程,重在收获。
其二,“在场”与时间的关系,因为“在场”是鲜活的即刻的,所以一定常常是写当下的现在的时态,但是小说的故事却是绵长的,不仅有现在,还有过去,还有历史,怎么处理过去的时态,让它们也同样有“在场”感,要消除时间与时间、今天的读者和从前的故事之间的隔阂,也是这部小说的难题。
所以,《江山故宅》在结构上是比较跳突的,由五个部分的正文和五个部分的附录组成,附录多为历史故事,正文则是现在。正文部分以“我”(言子陈)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附录部分使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但是“我”(言子陈),却多次出现在历史的故事中,在过去的日子里,她不时地跳出来,貌似突兀地说话。
比如第二部分的附录,写的是过去时间里的常随香老太太,但是中间又有今天的言子陈多次的发言:
常随香正在叙述:
他们围拢来,围得水泄不通,我想钻出去,却连条缝也不给我留,眼看着我被这帮无聊的邻居像绑架一样架住了,走不出去,我心里着急的,我不能错过我的时辰,不过还好,老话说,命中有时终会有,救星来了。救星就是我。救我奶奶的就是我。我叫言子陈,绰号“青肚皮猢狲”。这种绰号,一般是用在男孩子身上的,而我是个女孩子。我奶奶的叙述,本来就是我写的,奶奶正讲得起劲,我横戳枪出来显摆自己的功劳,我是怕大家只顾了听我奶奶乱讲,误以为我奶奶就是“我”,忘记了真正的“我”的存在。我对那些人说,你们这帮赤佬,真是闲出蛆来了,围住一个老太有什么意思,老太面孔上又没有花,只有汽车路,从来只有大人骂小孩子“赤佬”,我一个中学生,却喊大人“赤佬”,他们也是头一回碰头,气呆掉了,趁他们呆若木鸡,我连搀带拖,把奶奶从邻居手里抢了出来,送到大门口。吹了一声口哨,腿一甩,骑上自行车走了。
这是用心结构、用心设计的,正文部分比较好理解,就是以“我”(言子陈)的视角讲故事,附录部分也有言子陈发言,主要是加强“我”的在场感,也希望这样的穿插,能够让读者更有代入感,即便在“附录”中,“我”(言子陈)也一直都在,通过使用现在时态,在过去时的叙事中营造出“眼前发生”的感觉,以消除时间造成的隔断,努力让读者跟着“我”在现场寻找、判断和思考。
其三,作者的“在场”和人物的“在场”。为了让作品中更多的人物“在场”,在作品中建立一种“存在感”,让读者感觉到,哪怕是历史人物,他们也都活在当下,都“活着”。
小说采用了多视角,多形式,使其成为一部复调小说,多声部小说,文体上的多样性,是由多种文体构成的一部“杂色”的作品。
比如书信、日记、传记,口述实录,评弹脚本,等等,一方面,这些文本的参与使小说的叙事体式更丰富,另一方面,它们对应着不同的人物,用适合的形式表现不同的人物,试图让人物更加鲜活有个性。
比如写到余白生,从受伤失忆,到恢复记忆,儿子余又始终都“在场”,从来没有离开过。
“其实当我一切正常以后,我恢复了独自行动能力以后,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是会提到余又的,我经常提到他,来温暖我自己。比如我会去离家比较远的陌生的澡堂子洗澡,我会买两张浴票,看门人问我一个人为啥买两张浴票,我会说,余又在后面,一会儿就到。再比如,我去吃汤包小馄饨,我也是点两份,我吃完一份走的时候,会关照那一份不要动,等会儿会有人来吃的。”
父爱,深情,始终都在,每每不经意地在平凡普通的生活中呈现出来。
不仅当代的人物在场,历史人物也在场,逝去的人物也在场。不仅人物在场,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在场。
写作,要努力让读者一起走进来。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原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