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冯 娜
陈崇正《时光积木》的出版,可视为是一位曾经的校园诗人踏上漫长的小说道路,良久耕耘,依旧对诗歌初心念念不忘。“时光”与“积木”这两个意象的并置,已经昭示了这本诗集的基调:在时光隧道中回望那些童年的欢愉与失落、青春的燃烧和寂灭;以搭建童年积木般的耐心和热情在生命历程中搭建着自己的梦景和渴望、塑造自己的多重面影及可能。这是一本回望之诗,也是一本对生命之河的回溯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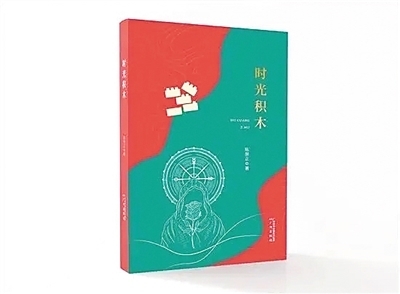
《时光积木》 作者:陈崇正 版本:广州出版社时间:2023年3月
时间在诗人的生命中并非只是线性的流逝,正如陈崇正在诗歌《神秘情感》中所写“所有我们遍历过的那些话题/周而复始,与时光同行”;与时光同行的,不仅是一代代人如西西弗斯一样难以解脱的话题;还有生命个体的纷繁体验和感悟。“给我一点时间/我现在只是一颗种子/给我一点时间,我会长出来/我会长出叶子,再长出粗粗的枝干/最后在枝干上生出隆起的疙瘩/再长出刺,一根根的刺,刺向天空和大地”(《石头正在裂开》)。时间对于世间事物而言,意味着运动和变更,对于诗人而言,时间意味着生命的渐进和“分裂”。陈崇正的小说书写中多次以“分身术”这类手法暗示人如何获得多重身份体验、命运又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他在意个体生命的层次感和交互性,这与他的诗歌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和互文。比如他在小说中写到的碧河、松山湖、潮汕民间风土等地理元素,在诗中也有新的呈现:“在路上/生和死逐渐了然/唯一丝怀念可供独享”(《碧河小调》)……与小说不同的是,诗歌中这些地理元素更像是一个人重返自己的精神原乡,它们像幼年的积木般散落在岁月的某处,在一堆沙地上等待着它的主人将它们重新擦拭、抚摸和垒砌。
——这类似“沙之书”的垒砌耗费了陈崇正众多光阴,其间,他走出了潮汕、再走出松山湖,并在线性的小说叙事中完成着自己的另一个分身。在绵密的日常中,他感到时空并非全然是单向行进的,“时间如同掰开一个橘子一样/将我一分为二”(《石破天惊》),时空在折叠和变形中塑造着诗人心灵的形状,《要学会看夕阳》《日子以东的遗老》《变黄》等诗歌,无不表达着陈崇正对时间这一母题的思考,同时浸透着对生命的敬畏、对无可挽回的消逝的感伤。
在《时光积木》这本诗集里面,陈崇正选择了不同的地理意象和物象来讲述“成长”和“时间”这个主题,我想这是一个日趋成熟的写作者渐渐接近了他心灵的对等物。这对等物,在他过去的小说当中是以碧河、潮汕这些稳定的形象呈现的,但在《时光积木》这部诗集当中,这些形象开始虚化、漫漶,溢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叙事;这也意味着陈崇正有意识地走出了地方性的苑囿,不再流连于具体的地理空间书写,而是开启了携带心灵物象的旅行。
这种写作倾向与陈崇正以及诸多学者、作家热情提倡的“新南方写作”的精神气象是不谋而合的,“新南方”不是单纯“南方以南”的地域性书写,而是意在塑造一种新的南方人文精神,将南方新兴、杂糅、生动、陌生化的气韵融入更广大的文化格局中去。过去的南方诗歌的写作曾为我们出现过非常多的“热词”,比如“打工诗歌”“工业诗歌”“城市诗歌”等等,而《时光积木》等南方新诗集的出现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美学倾向并塑造出新的南方元素、建构起新的南方形象呢?在这些新的审美体验和表述中,譬如碧河镇、一年一度的清明诗歌(陈崇正称自己的家族没有清明拜祭的传统,故以每年写一首清明诗作为内心的仪式)、大海在其南等书写是否又为我们提供更具普遍性的经验和观照呢?这是一个写作者必须思虑的问题。
记得小说家王安忆曾经说过一句话,她说一个作家的处女作代表了他对世界的困惑,而一个作家的代表作则代表了他对世界稳定的看法。在《时光积木》这本诗集中,我们已然看到了走向不惑之年时陈崇正对自己的故土、童年、青春有了更为成熟和稳定的看法。
诗人陈崇正在诗中体现了比小说家陈崇正更为感性、浪漫、纯粹的一面,就像一个远行人在风尘仆仆归乡时,在碧河前的桑树下得到了阴凉,他感到喜悦,同时感到松弛。“这是幸福的季节,每棵桑树都是新的/内心积攒多年的欢喜一并涌出/ 哦,夏天,神的赐予/那些甜甜的桑椹,带着酸酸的回忆/和温柔的爱意一样/都是我们来到人世最好的礼物”(《桑树》)。这首诗让我想起了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如果一个人能对生活始终心怀感激并看到生命深处涌动的爱意,那么,他一定会是一个幸福的人。而这个幸福的人手里还握着一个掰开的橘子——时间正向他敞开更繁复、迷人的篇章,这一瓣瓣橘子是苦涩还是甜美呢?碧河正缓缓淌过时光的积木,向更深远处流去。(冯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