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唐 山
“这世上的事,从来都不是按照你想的那样,先有原因,后有结果,跟下棋似的,你下一步,我下一步。不是这么回事。事情如果应该发生,它自己就会发生。我们用不着预先替它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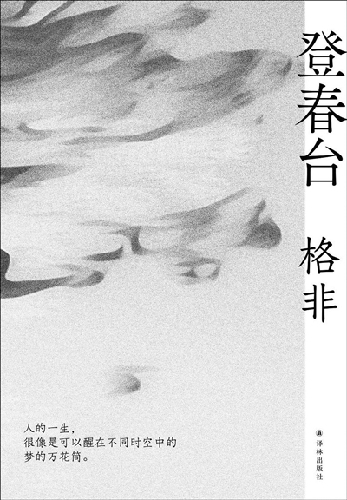
在格非新推出的长篇小说《登春台》(译林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中,四个主角之一窦宝庆对郑元春这样说。窦宝庆意识到,郑元春对他有意,他该表现得更“野蛮”一些。只是没想到,这场不伦之恋将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登春台》是一本有趣的小说,它的细节是写实主义的,主题却是现代主义的。小说从四个人物的视角展开(其中窦宝庆的部分采用的是第二人称“你”),刻画了四次平凡却内涵波澜的人生——表面光鲜,却各有无法弥补的遗憾。
《登春台》像四片随意采摘的树叶,鲜活、生活、饱满,却有共同的忧伤——无根。由此衬起小说标题中隐含的反讽:《登春台》典出《老子》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意思是“生活在幸福的太平世界里”,如果找一个词来概括过去的40年,“登春台”可能最妥帖。
然而,《登春台》中的每个人真是“如登春台”吗?我们真的找到了自己吗?
是幸运,将他们带上了波峰
表面看,《登春台》中的四个人物都特别幸运。
沈辛夷是留守儿童,母亲更喜欢她的弟弟;父亲虽温情,却多病,在家中完全处在从属地位。沈辛夷的生活没有任何浪漫成分,即使看上去挺文雅的名字,也仅因姨妈看到了门前的辛夷树,随口起的。她后来又看到了泡桐树,则沈辛夷的弟弟名字就成了沈新桐。
作为被一再忽略的人,沈辛夷上初中时春游,被成年人猥亵了。这让她成了全校议论的焦点。她的母亲找到学校大闹,只为获得赔偿。当母亲将其中的1000元(都是新钞)给沈辛夷“随便花”时,她并没觉得“得到了补偿”——最关心她的老师因该事件被调到乡村,从她的生命中消失。
高考时,沈辛夷偷偷修改了母亲填写的志愿,被北京外国语大学录取;以后,她考上了研究生;经历波折,她进了一家大公司,完成了“小镇做题家”的命运逆袭。
陈克明来自北京郊区,毕业于民办三本学校,名义上学数控机床,其实只是领了一本教材,从没上过课;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哥们儿帮助下,做各种小生意。父母给他介绍了一名叫尹静熹的女孩,无父无母,舅舅将她养大。一半是同情,一半是贪图美貌,陈克明与尹静熹成了夫妻。尹静熹超级嫉妒且强悍,但判断奇准,在生意上几次提出正确意见,只是陈克明屡屡错过机会。
陈克明的生意一败涂地,不得不“开黑车”维生,意外遇到神州物流公司的老总周振遐。后者欣赏陈克明的沉稳、精明、负责、有活力,将他拉进公司,从普通司机一跃成高管,甚至一度想把他培养成接班人。
窦宝庆来自甘肃的一个贫穷的小村,稀里糊涂来到北京,成了长途车司机。他所在的公司恰好被神州物流并购,他因为长得高、沉默寡言、为人忠诚、开车技术好,被筛选出来,当周振遐的司机。其实,人力资源部完全不了解窦宝庆,仅凭仓促间的直观印象,便做出决定。窦宝庆深得周振遐的欣赏,一度也曾想培养他当接班人。出乎意料的是,公司高管、富婆郑元春看上了长相帅气的窦宝庆。二人开始了一段恋情。
周振遐则天生好运。他性格恬淡,本是学者,充满活力的大学好友蒋承泽创业,将他拉到公司中。蒋承泽因癌症去世,周振遐成了一家大公司的“老大”。在他管理下,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这四个人俨然是“成功四重奏”,无数人曾如此向上攀爬,时代也似乎给了他们足够的回报。但事实上,每个人的“成功”都源于侥幸,却被解释成“必然如此”。
他们只是假装正在“登春台”
其实,所有的光鲜都有背面。
沈辛夷一生试图躲开她那无比强悍的母亲。母亲不断在创业,不断在失败——每次失败后,她又会东山再起。混得好时,她会带全家去大宾馆“享受”。可拿起菜单半天,仔细研究了上面的价格后,又决定带全家离开。她让沈辛夷用火腿肠、方便面充饥,以等待宾馆的免费早餐。母亲的字典里没有“体面”二字,她被受穷的记忆追逐,永远停不下来。
沈辛夷从没感受到母爱。上大学时,为了帮母亲借钱,她接受了一个北京老头儿的包养。老头儿有一个小四合院,充满情趣,他自称是“人生的观察者”,不工作,不动情,只是旁观。即使沈辛夷哭闹,希望确定两人的关系,他也不置可否。慢慢地,沈辛夷意识到,老头儿的悠闲中暗藏着一种绝望。3年后,他果然上吊自杀了。
沈辛夷试图说服自己“母亲总是母亲”。当母亲再次创业失败,且身患癌症时,沈辛夷试图留下来照顾她,却发现,母亲正在算计沈辛夷还有多少钱,她要再搏一把……
陈克明转运后,努力提醒自己,和尹静熹是患难之交,不应背叛她。可一次“一夜情”彻底摧毁了他的信念。他这才发现,自己生命中早被内置了无法挣脱的自毁按钮——明知不应该做,却偏偏去做。正如他的表哥所说:“凡是私底下在黑暗中发生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都是那么的激动人心!”它就像咒语般,套牢了陈克明的人生。尹静熹离开了陈克明,成了他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活着突然变成“只是活着”。
窦宝庆沉迷在郑元春的爱中,却不知警方已悄悄收紧线索。在老家,为了自杀的姐姐,窦宝庆杀了仇人,躲到北京,却意外混出了模样,成为村人眼中的“大人物”,也引起警方的注意。窦宝庆以为,“事情推着他走”的好运将一直持续,没想到郑元春要他讲故事。不会讲故事的窦宝庆只好把姐姐的遭遇,装扮成故事,讲了出来——可警方早已对郑元春做了工作。就这样,窦宝庆暴露了自己。以为早已翻篇的那个世界,又将他拉了回去,让他进了监狱。
周振遐似乎生活在云端。可他是一个如此沉迷于安静、不喜欢被打扰的人。他想把窦宝庆、陈克明培养成接班人,仅仅因为他感到厌倦,不愿再背负企业家的责任。周振遐试图用种月季花找到自己,但随着蒋承泽曾经的情妇姚芩闯入,他又陷入各种关系的牵扯中。
在《登春台》中,人人都在漩涡中挣扎,只是看上去“如登春台”。他们似乎正在掌控人生,其实只是一个个幻象,除了忽悠人们更深地卷入之外,别无意义。
一切皆无答案,只有不断装蒜
在我看来,《登春台》的主题更像格非早期的小说,直面“我与世界”“我与他人”乃至“我与我”之间的冲突。人人努力将不确定的生活纳入到“发生—发展—高潮—结尾”的叙事中,可越努力,就越暴露出自身的无能。
因为,现代化重塑了时间,曾经的循环已被打破,万物皆成奔涌而出的狂奔状态。所以,格非写道:“在过去的生活中,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赤裸裸的、让人难以承受的‘坏’,也存在着不容辩驳、完满如期待的‘好’。而在今天,我们既没有不可接受的‘坏’,也谈不上什么确凿无疑的‘好’。如果你非要再说一件事情‘好’,那也只是看上去如此罢了……到了今天,这种循环让位给共时性的简单叠加,‘好’也悄悄地让位给‘多’。”
让沈辛夷们无法圆满的,正是他们不得不经历的“多”。除了忘却,还有什么能化解“多”的压力呢?“它实际上处在一种失重状态,给人带来犹如电梯急速下坠般的眩晕感。无论是人还是宇宙,都成了浮泛无根之物”。
在沈辛夷们的背后,其实还有更丰富、更冰冷的“多”:
沈辛夷的父亲多病,不得不忍受妻子的坏脾气。他应该已猜到,妻子和小老板之间的肮脏关系。带窦宝庆出道的胡爱民,执着于传统“带头大哥”的交往方式,他会怒骂窦宝庆的技术不过关,却又在生活中照顾他,包括在跑长途的路上帮窦宝庆找妓女。他不知道,窦宝庆绝不会为此感恩。当胡爱民身患绝症时,他的借钱求救短信被窦宝庆无视。陈克明接了一笔大单,不顾妻子一再暗示,拉岳父入伙。结果陈克明将几年的收入全赔了进去,岳父却悄悄买了奔驰汽车,找了高个儿女人……
《登春台》如万花筒,呈现出变动时代的丰富面向,却始终围绕根本之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由此揭开血淋淋的真相:那些似乎可以设计人生意义的人,早已将灵魂抵押。他们只是关系万千重下,被塑造、被扭曲、被决定、被引领的“空心人”——也许,人生的快乐与苦痛的比重是恒定的,不断在变的,只是不同的呈现方式。
感动于《登春台》,是因为它内蕴着无边的悲悯:没有人能真正把握自己,没有人能真正逃出这个困局,没有一种生活是毫无遗憾的,也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可爱的。
那么,该何去何从?
当沈辛夷明白她永远无法遏制母亲的雄心壮志时,她选择了离开。“她搀扶着母亲走下那道陡坡,最终停在了路边的那棵孤零零的大樟树下。她们在树下道别,辛夷拼命地克制着想要拥抱她的愿望。就这样,母女俩一个往西,一个往东,一个上坡,一个下坡,渐渐地就隔得远了”。
也许,《登春台》真正想说的话就是:不论活多少次,人生总会是这个结果。(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