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李 言
张柠教授在《故事的过去与未来》一书中,展现了一个学者高超的文学感知。《故事的过去与未来》分为“中国故事形态”“讲故事的方法”“城市的馈赠”和“数字时代的文学”四个部分,从东方到西方、从远古到当下、从乡村到城市,张柠以宏大的文学视角和极具灵性的洞见,为我们重建中国叙事的无限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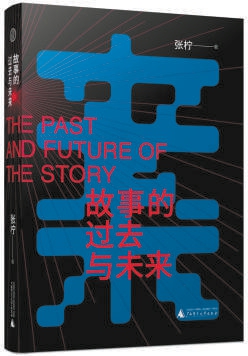
《故事的过去与未来》张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叙事的传统走向
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生产形态中,中国人的起落、生死和自然构成了统一的状态。人依天时而生产、依土地而生存,对耕地资源的持续索取,是古人财富增长的重要方式,因此在以二维空间为核心的文明样态中,对“平视”资源(土地、房产、家畜)的持续物欲,构建起中国社群文明的基本秩序。可见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中,多以现有秩序为根基、对现有秩序的依存和确定,为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重要传统。
而在耕地为生产资料的散落社群中,村落产生了。村落可以看作农耕社会“平视”资源在家族和血缘中物的外化,由此村落产生的叙事形态即以现有“时空体”为根据,完成对故事的显现。故事表述模式便为:现有时空的叙事表达、对过往的追溯、对逝去时光的缅怀,张柠定义为叙事“时间的权威”。
在顺天而为的生活理念中,中国人其实蕴含着对永生的永恒渴望。如果女娲造人定义了人的存在价值,人的叙事价值则蕴含在土地的过剩劳作中,即以终结泥土生长性的塑形方式让生命永生。张柠则以青花瓷这一器物为例,图案符号的叙事性即东方叙事的典型,且让时间终结,让空间被叙事重构。
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与天时形成暗合,这在古典小说中尤为明显;封建文明末期对土地依赖的加重,体现于文学表达的时空体中。无论是《西游记》《水浒传》还是《三国演义》,皆以圆形为核心表述形态。圆形分为时间的圆和空间的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时间圆形,用一句话概括则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时间的圆。《西游记》则具备时间的圆形属性,小说借想象力实现经验的扩张,即张柠所提到的“幻想家叙事”和“创造的权威”。但在取经这一跨国族地缘行为中,结尾的“还经”意味着空间圆形生发的必然性,从长安出游,终以“归程效应”返还长安,其实长安在小说中不仅具备地理属性,它是皇城,更代表着皇权、封建文明的权威以及农耕法则的最高秩序。
空间变革下的现代性叙事
张柠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乃作为皇宫的陪衬而存在,但19世纪后期现代性在中国城市发生,瓦解了以土地为根基的叙事样态,以自足性和圆满性为特征的圆形叙事小说被现代文明冲撞,古典小说的固有存在模式被打破。陈平原教授在对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划分出多个派生的新类型,这背后是中国文人对特定时空准则的认知破除。可见,原生的空间权威被闯入的现代性所动摇。
首先,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后介入中国社会的走向,远行和远航成功倾销了帝国主义商品。依据天时法则生存的中国人被外来世界冲撞,“震惊感”是外部赋予的。震惊既是心理效应,又是文学效应,叙事学表述为“叙事经验”的增益,张柠定义为叙事空间的权威的变化。空间的权威传递着叙事模式的变革,冒险精神、自由思想和个体英雄主义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诞生。
其次,空间的权威与航海文化的联结,加速了叙事多样性的产生。海洋的无边界性、扩张性和不确定性其实早在西方古希腊时代便已经显现,其代表是古代城邦的建立和民主政治的兴起。资本主义的产生让海域由内海向外海扩张,一度围绕地中海而建立的海洋文明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世界海域均成为西方国家活动的场域。在张柠眼中,清朝末年欧美人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城里人”的地位,成为世界“显形”的主导者。
毕竟,航海时代的叙事是冒险性的、征服性的、背离土地精神的,这与凭土地建立起的叙事样态完全相反,关于文学的表达被注入了新的力量。就形式上说,出现了报刊连载式的文学;就类型上说,出现了科学幻想类的文学体裁;就内容上说,城市人群样态的书写被日益挖掘,获得了新的空间权威,中国小说不再只是关于古老的英雄叙事和圆形结构的塑造,一种悲伤的、无边界的、游荡的小说类型诞生。
中国小说的现代性被空间改变,晚清小说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如以科学幻想为主题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以城市世情为主题的《海上花列传》、以游历见闻为主题的《老残游记》等,这是农耕文明向现代转型的文学印证。
最后,比起生产模式的变革,城市生活模式也影响着叙事的转变。空间权威的引导加上空间形态的转移,即现代城市在中国社会的诞生。中国的现代城市多为通商口岸,依江而建,借水而生,中国原有的宗族式居住模式被改变,上海、武汉、天津等城市的兴起,水的流行性与城市人群的流动性构成了从空间到心理的契合,城市人群的游离感和孤独感也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呈现,赋予了小说自我表述的现代性。小说为城市的精神写照,这以穆时英、徐訏和施蛰存的小说为代表。
关于中国叙事的反思
张柠认为,比起西方的社会建构,中国古典城市文明的建构中,包含着对农耕之外世俗生活的否定。但西方化的城市和东方的农耕形态共同且长期存在,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重要表征。城乡二元文学在一百年间不断割裂、反刍和融合,对中国叙事的反思也因城乡二元化而起。由此,关于中国叙事的建构亦经历了如“乡下人进城”“逃离北上广”“乡村振兴”等特色文学命题,这似乎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宿命。
回顾20世纪中国叙事史,它在进入现代城市后经历了彻底的变化。其中依托城市文明建立的大众传播和文化消费的兴起,使得传统小说在城市文明中获得了新生。
首先,新小说借助现代出版业和报刊发行业等载体,在城市中传播迅速,中国文学的商业模式在大都会中产生,以包天笑、张恨水、周瘦鹃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市民文学)在城市文学中留下一席之地,这为当下网络文学的兴起提供了本源性案例。
其次,在总结中国叙事史层面,鲁迅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这一有影响力的专著,它道出自古以来的故事发展形态,指出小说形态变化的脉络。这一演变正是农耕文明从开始到确立、再到兴盛、最后衰败的过程,背后与中国社会的叙事特性息息相关。
最后,在对小说传统的章回体桎梏破除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到来,左翼文学、城市文学、新文学在中国获得了充沛的表达空间。小说形态的创新由此持续发生,比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便以日记体书写小说,扩展了文学书写方式的多元性。
如今我们回看当下严肃文学,正是城市现代性与文学化学反应催动的结果。张柠的《故事的过去与未来》是对中国叙事面貌的精确显现,借用书中一句话来结尾:城市对我们给予了馈赠,现代文学写作,就是城市的馈赠。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