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李怀宇
扬之水只有初中学历,后来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她的经历曾被简化为“开过卡车,卖过西瓜”,自认准确的说法是:当过售货员,也当过司机。以她独特的经历,何以成为学者?这漫长的问学之道,值得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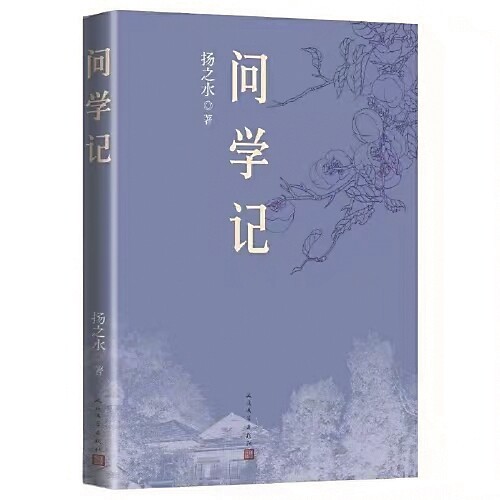
因为与大学无缘,扬之水走上自学的路,漫长的路途中不时出现指点迷津的师友。1984年春,新成立的光明日报出版社招聘编辑,录取的九人中有扬之水。编辑,自然要组稿;寻找选题,自然要海量读书。一年半之后,扬之水进入三联书店《读书》编辑部。顶头上司沈昌文是一位喜欢读书并且很会读书的人。《读书》十年,沈昌文对扬之水的奖励,是赠以她喜欢的书。而扬之水为组稿而读书,更是广结书缘。
扬之水在《读书》十年的日记里,几乎有闻必录。她记录徐梵澄的故事,颇具魏晋风度。徐梵澄早年自费留学德国,五年后,战乱家毁,断了财源,只好归国,在上海与鲁迅相识。1948年到印度教学,1978年返回阔别三十年的家园。扬之水认识徐梵澄后,徐梵澄坦白而诚恳地说:“希望你能常来。我一个人是很寂寞的。”有一次还说,扬之水是他唯一能够谈得来的女朋友。
扬之水问学的前辈中,我多次访问辛丰年先生,读来格外亲切。扬之水说:“和许多爱书人一样,他爱书也爱得入迷,除了音乐,也爱其他的艺术。并且,对历史、对哲学,对阶级斗争、政治运动,都有广泛的了解,大有老杜‘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之概。又似乎对新文学史尤其有兴趣。”辛丰年“每听完一部交响乐那样的大曲,如同读了一部《红楼梦》或是《战争与和平》,仿佛经历了一次人生,做了场黄粱梦”。扬之水理解辛丰年的个性:“他的善良并未妨碍他发现世间的非善。他不善于史中读史,却善于史外读史。他便清醒地‘梦游’在音乐世界,读人类历史,看世态人情。他为历史配乐,他为人生配乐,他在旋律中读到历史的真实。‘时靸双鸳响’,‘腻水染花腥’,凄美中的惨烈,也是一般春秋史笔。配了乐的历史与人生,便如这梦窗词中意象,带了特定的标识,定位于受过磨难、企望不再受磨难的心灵。”辛丰年的治学之道,与扬之水相似,细读不免心有戚戚。
金克木与辛丰年一样渊博,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生活中却是另一番气象。金克木几乎是不买书的,当然也没有书房。扬之水去拜访金克木,但见:“北京大学朗润园的金宅,一几,一榻,一张写字台,一个唯底层疏疏落落躺了几本书的书架,一个坐下去就很难站起来的旧沙发。”金克木不藏书,却有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脑。
回顾学思历程,扬之水说:“八十年代令人感念不置者,对我来说第一是对学历的宽容。初中学历,却能够凭着一支笔,凭着对书的爱,进入光明日报出版社,进入《读书》编辑部,并且不以学历低而成为工作的障碍,而且,我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特例。”治学,扬之水给自己设定的理想是:用名物学构筑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它是对“物”的推源溯流,而又同与器物相关的社会生活史紧密相关。它可以是诗中“物”,也可以是物中“诗”,手段角度不同,方法和目的却是一样的。
扬之水为文物定名,通常像破案,或者说是不断追寻证据的过程:发现问题,寻找解决的证据,一个一个证据形成证据链,疑案也就破解了。细读扬之水的《问学记》,对一个初中生能成长为研究员的疑问,也在这些活生生的学术证据中豁然开朗了。(李怀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