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汪涌豪
向不断变化的生活敞开
当我11岁时,开始做文学梦,大洋彼岸已有人在新出版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以下简称《影响的焦虑》)中炸响了“审美自主性”原则,并强调文学批评是一门艺术,它关注的是经典,而人只有调动自身的审美力量才能渗入经典,这个力量包括认知能力、原创性以及丰富的语汇等。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五六岁就立志成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终其一生都在反对包括解构主义和哈利·波特文学在内的文坛斗士,人称“抬杠批评家”的哈罗德·布鲁姆。其时他43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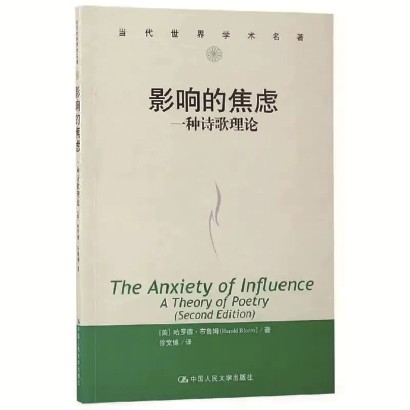
《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美]哈罗德·布鲁姆 著徐文博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在书中,他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深入剖析了传统对创作的多重影响,指出前辈诗人因先进入历史,不免对后辈的创作形成阻碍,并使之产生焦虑。后辈若要克服这种“影响的焦虑”,就必须努力把前辈及其作品从传统中分离出来。记得博尔赫斯《卡夫卡及其先驱者》曾称,每位作家都创造了自己的先驱者,作家的劳作能改变人对过去甚至未来的理解,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也认为,已有的不朽之作联成一体,一旦新作加入这个体系,就意味着与传统达成一致。但布鲁姆颠覆了他们的说法。在他看来,传统不是一个完美的体系,后辈承继前辈也并非文学沿革的常态。事实是,他们不可能因循守旧,相反,只有藉焦虑激发的动力去找寻新路,以向不断变化的生活敞开。准此,他认为一部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史,就是压抑与反压抑、焦虑与反焦虑的历史。
“选择一条英雄之路”
多年后,我在课堂上引用这个观点,心里有一种特别通透的爽快感。当时的认识,传统可不就是既有过去性又有现在性。因为传统,后辈作家才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和前辈并存的秩序中,当然,他会因此感到压力山大。对此,布鲁姆用“弗洛伊德式的挣扎”来形容。他特别呼吁后者要有创造力,认为这种创造力不是对过去的感激之情,一个伟大的作者若想与传统先驱或自己的文学祖先竞争,就必须有所创造,像撒旦一样“选择一条英雄之路,去经历地狱之苦,去探索在地狱里可能还有什么作为”。他认为弥尔顿就是这样的人,他用有意藏拙和隐藏原型的方式来抵御焦虑、对抗影响,《失乐园》的主题因此就成了他与撒旦之间的争斗,正如《哈姆雷特》的主题是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之间的争斗一样。此外,先贤与前辈大多高明,决定了与之正面相搏必须是隐蔽的,所以他进一步提出应用反讽、提喻、夸张等手段来实现误读,用偏离前辈和虚化自我等策略来修正原作,以便使它们脱出时间的挟制,以独立的姿态接受后人的审视,直至这个后人最后削弱与消解从前人处所承继的影响。
为此他鼓励后辈应勇敢地与前辈的权威文本争夺影响,认为文学正是有抱负的作者在面对伟大前辈时,因害怕失去创造力而内心焦虑的集中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主张的“影响力的焦虑”,实际是作者对创作灵感的一种特殊祈求方式和回应方式,而“误读”因此也与“焦虑”一起,成为他理论中最重要的关键字。如前所说,他称西方诗歌史是一部压抑与反压抑、焦虑与反焦虑的历史。至此,他则进一步指出,它还是一部“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直到31年后,他编选大型诗歌选本《最佳英语诗歌:从乔叟到弗罗斯特》,仍坚持认为诗的历史形成于后辈诗人对先驱的误读与曲解。在为此撰写的导读《读诗的艺术》中,他称诗的本质是一种“隐喻性的语言”,而伟大的诗尤其能让人察觉到一种“殊异”,从而助人成为“我们自己的自由艺术家”。
为强调这一点,他甚至无意撇清这种自我成长与将对象“妖魔化”的关系,认为所谓影响正意味着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妖魔化”的误读或曲解,所有的阅读和批评实际上都是误读或曲解,文学本质上就是作者在反抗传统的过程中,通过语言展现无限创造力与无穷生命力的活动。可以想象,这种义无反顾的彻底的主张,对一个尚处在遏制不住奇思异想、独任自我时的我有多大的吸引力。它鼓励了我,让我相信在将要到来的岁月里,自己对一切伟大经典的阅读与批评是可以恭顺谦和与桀骜不驯并存的,并且有时候唯桀骜不驯才是真正的恭顺谦和。
说起来,误读现象在中外文学史上都很普遍。不过在西方,人们对它的认识通常从读者出发,以对偏见的分析作为阐释与论说的起点,来证明有此现象实属必然。当然也有从文本出发,结合语言的差异性与修辞性,从反方向证明正读之不可能的。但布鲁姆不这样,他从作者角度切入,用弗洛伊德家庭罗曼史理论,结合尼采超人意志论、希伯来神秘哲学、保罗·德·曼的文本误读和弥尔顿以来英美浪漫主义的诗学实践,将作者因阅读前辈产生的心理焦虑看作是误读发生的根本原因,突出强调误读所隐含的否定性价值和创造性品质,由此创设出那个时代最大胆、最有创见的理论,“震动了所有人的神经”,一时主张以批评介入社会的女性主义和种族理论批评等流派,都不得不避其锋芒。在随后推出的“诗的误读”四部曲的后续三部曲《误读的地图》《卡巴拉与批评》《诗歌与压抑》里,他不断丰富、修正自己的理论,最终确立了以“对抗式批评”为宗旨的诗的误读理论。其间,作为犹太移民的后裔,他与美国主流社会的紧张关系,为他的诸多观点定下了个性鲜明的基调。这种基调在此后的发展中不仅不断凸显着仅属于他个人的文化身份与诉求,更昭示了他批评理论的人文主义本质。所以,他被称为西方传统中最具天赋和原创性、煽动性的批评家。《纽约时报》书评版主编萨姆·坦侬豪斯称他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文学界最为多才多艺,也是最刺激的存在之一”“兼具学者、教师、评论家、散文家、檄文执笔者等身份的奇异品种”。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在向英语读者介绍现代法国诗和实验小说方面极具影响的普利策诗歌奖获得者理查德·霍华德,甚至直陈长时间以来西方人一直在接受他的教育,并称他是“活的百科全书”。而我只有感叹,当自己为这样的百科全书深深着迷,已在20年后了。
用全部的身心来读
近些年,关于他的著作,个人心有戚戚焉的更是在这个技术时代,他对必须阅读文学经典的一系列论述。体认到批评不仅为获取文学知识,还是一种社会参与行动,其最终目的是要教育大众影响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起,他更多面向大众,不断向人强调文学经典的原创性、陌生性和审美自主性的意义与价值,呼吁人在经历了对文学做道德化、政治化的过多解读后,能重新回到经典本身,甚至总结出阅读公式,教人如何发扬审美主体性,在体认经典的创造中实现属于自己的审美有效性。他告诉人们,艺术来到你身边的时候意图很坦诚,就是要赋予你的时间以最高的质量,因此阅读的目的就在于“寻到更真实的自己”,从而增强和改善自己,实现“内在自我的扩展”,为此他写了著名的《西方正典》一书,通过对莎士比亚等26位伟大作家的解读,揭示经典的奥秘。
在第一篇《论经典》中,他明确表达了自己以审美价值为核心的经典观。众所周知,英文“正典”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原指织工木匠使用的校准棒,后延伸指法律或艺术的尺度规范。他认为经典之于今人仍具有范式意义,所以之后又写了《如何读,为什么读》《天才:创造性心灵的一百位典范》和《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等书,不遗余力地呼吁人“必须有能力用人性来读,用你的全部身心来读”。直到暮年,《记忆萦回》这本文学回忆录仍收录了他对《圣经》等80段文本的解读。书中尽管《影响的焦虑》中常见的焦虑、误读等关键词不再出现,但它们所指涉的意义并未消散,相反,因仍致力于揭示“对抗与经典”和“陌生与崇高”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终究将误读理论贯彻到了最后。这份坚持,让脑子里始终有各种主义在跑马的我钦佩不已。
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他写道:“我继续写作是因为心中有一个史蒂文斯式的愿望,也就是希望我们内心伟大的声音可以往上升,与惠特曼的声音和莎士比亚创造的几百个声音汇合。对我的学生和永无谋面机会的读者,我总是力劝他们努力实现读者的崇高,要求他们只对能够让他们觉得永远无法穷尽的作家进行正面接触。”他和在耶鲁大学听过他课的诗人王敖聊中国诗,问的也是“中国当代有没有能够继承伟大儒家传统的诗人”,而不喜欢朦胧诗,这似乎可用来证明他希望与中国的伟大诗人“正面接触”。什么是“正面接触”?当然不是指找经典作品来读,而是指把自己放进去,并与之短兵相接。在我看来,这可不又是他终其一生都坚持直面伟大前辈,在经典影响和激励下发扬审美自主性,过一种精神性生活的表征?所以,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朗吉努斯的崇拜者。
以审美力作对抗式的批评
现在,我同样任教于大学,从事着与他一样的文学研究与诗歌研究。我几乎有他所有重要的著作,能感同身受地体认他对文学批评越来越分裂为低水平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不满,并对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只读拉康、福柯或德里达,却不读斯宾塞、莎士比亚或弥尔顿感到失望。还有,与他一样,也时常感叹批评不讨好,许多作家确实如他所说,“面对文学批评家甚至比对小说家或诗人还不自在”,但他仍能坚持立场,从未停止过批评,对此我真的佩畏不已,常怀有深深的敬意。他感叹在自己四十年的研究生涯里见过太多潮流来了又去,晚年终于能辨别出“哪些是转瞬即逝的水面涟漪,哪些是水底深处的水流,或者货真价实的变化”,我因此好希望自己也能有此慧眼。只是不敢确定,尽管自己从来崇拜纯美,但能不能像他一样虽千万人而独往,不顾一切地坚持唯美与浪漫的立场。
说到底,通过《影响的焦虑》一书,他教会了我重新认识文学批评首先应具备文学性,要既具个人色彩,又富有无限的激情。因为它不是哲学、政治或宗教,它渗透着批评者对生活的参悟,最需要智慧,甚至就是智慧本身。因为它所亲近的文学反映的并不一定是生活中最好的部分,而只是生活本身,甚至是生活最糟糕的部分。所以当黑暗袭来,价值破碎,就是需要人以自主的审美力作对抗式批评。
所以我愿意晚年与这个“幸存的古迹”为伴,相信他最适任经典文学的布道者,他关于经典的那些著作就是个人的福音书。这样,我就有可能不受来自文学外部甚至内部任何因素的影响——从消费文化的滥情到精英文化的固执,活到老,读到老,从而免于成为被他嘲讽过的那种人,他们虽然一直研究文学,其实既不喜欢文学,也不懂文学。
汪涌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美学的教学与研究,兼及传统史学、哲学与当代文艺批评。著有《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等专著13种,主编有四卷本《中国诗学》等8种。另有书评集《书生言》、演讲集《文明的垂顾》、新诗集《云谁之思》和旧体诗集《巢云楼诗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