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符 晓
在20世纪意大利文学史上,《豹》仿佛是一个秘密。其作者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既是兰佩杜萨亲王又是帕尔马公爵,一生辗转颠沛,仅凭一部长篇小说就获得了崇高的文学史地位,其小说本身谈不上扑朔迷离,却仅用几个片段就为读者渲染出一幅颇为辽阔的19世纪后半叶意大利贵族衰亡史,使读者在雕栏玉砌的新朱颜中感受历史的苍茫。因此,对这部小说的阅读和阐释,既是文学漫步,又是历史解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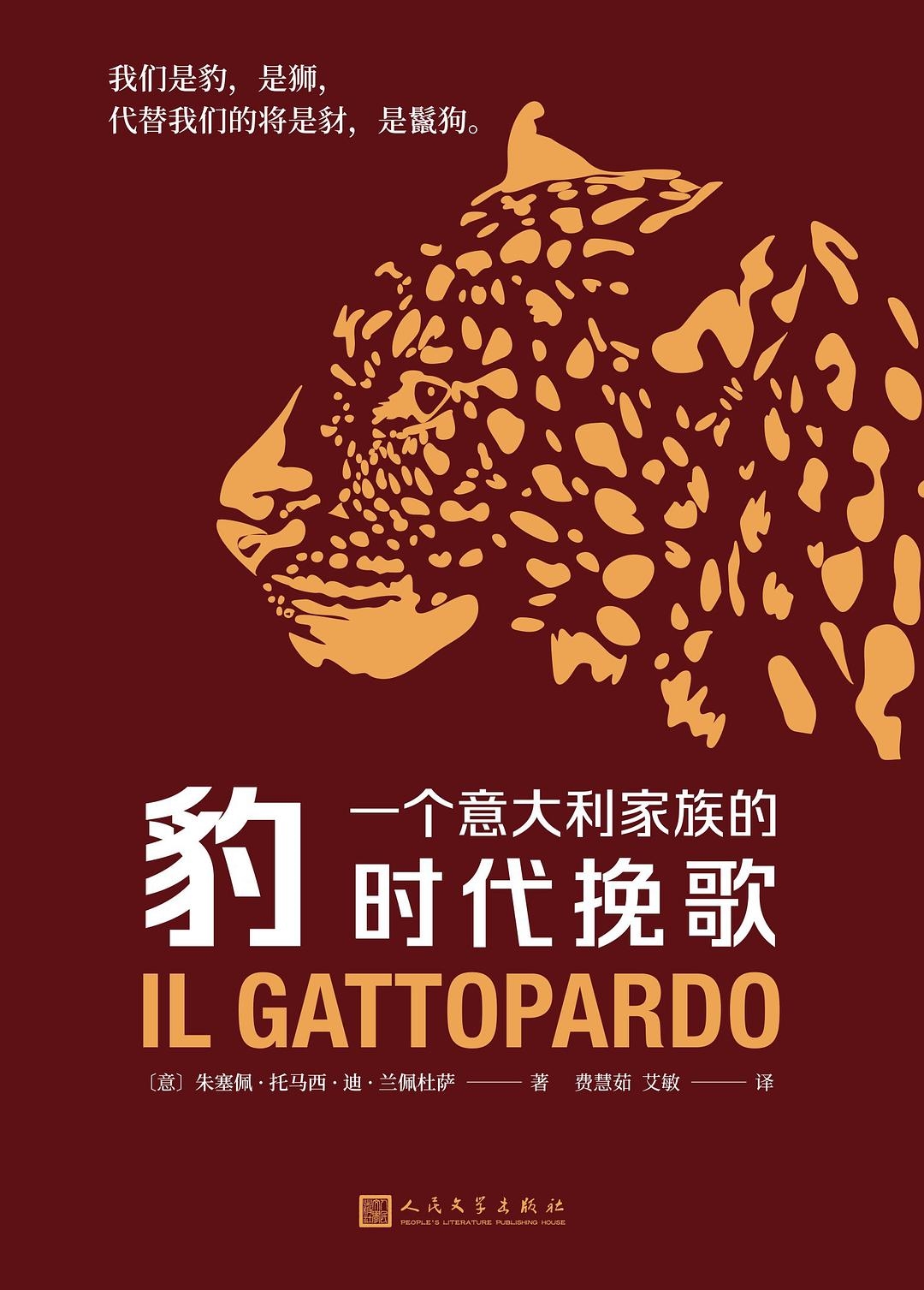
《豹》,【意】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著,费慧茹、艾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4月
“西西里干焦的土地在痛苦地呻吟”
故事发生在1860年的西西里岛,彼时距法国大革命爆发的1789年已经70余年,但是大革命的光晕即便在意大利也迟迟未散:前有拿破仑两次占领亚平宁半岛留下影响至深的社会制度遗产,后有1848年革命促使意大利人深切呼唤统一的国家,及至伊曼纽尔二世时代,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共同形塑了意大利的统一,而后者所领导的义勇军远征以及之后的“泰亚诺会谈”恰恰是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南部地区并入萨丁王国的重要事件。法布里契奥亲王的家族往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发生的。
谁是法布里契奥亲王?他可谓是西西里岛最重要贵族的领袖,其家族享受着贵族数百年来天然可以享受的荣华,高大的厅堂、华美的穿搭、佃农的“贡赋”、浩荡的车马,都成为亲王所代表的萨利纳家族的注脚。而在历史的褶皱中,贵族必然随城头大王旗的变幻而消解,事实证明,加里波第“红衫军”的到来和本已山河日下的波旁王朝统治的确使亲王家族漂泊在红尘之中。这也自然而然使人联想到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甚至二者所描述的关于家族衰亡的时间都具有相似之处,如果说曼的小说象征的是西方的没落,那么《豹》则意味着西西里贵族的衰亡。
其实,家族的没落纵然可悲,然而考虑到西西里岛在加里波第登陆马尔萨拉之后的历史处境,萨利纳家族显然只是沧海一粟。受地理位置影响,这座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先后受到希腊、迦太基、东哥特、拜占庭、撒拉逊、诺曼底和西班牙人的统治,对于生活在西西里岛上的亲王抑或其他生兹长兹思之念之的岛民来说,两千年来的风雨已然将其洗刷得满目伤痕,加之统一进程中的流血牺牲,使巴勒莫等地再次沉浸在不分敌我的战争和政治阴霾中。因此,兰佩杜萨所谓“西西里干焦的土地在痛苦地呻吟”,恰恰是风雨如晦的写照,也凸显出西西里不能承受的革命之重。
作为西西里的代言人之一,亲王恰恰经历了从波旁王朝向意大利王国惨烈的过渡,更具备感慨岁月飘零的资格,所以作者选择经由他的眼睛审视西西里。在他眼中,故土丰饶,“窗外的景色炫耀着自己所有的美丽”,“就连凶恶的巴勒莫城也围绕着众多的修道院,安静地躺在那里,宛如羊群卧在牧羊人跟前”,他当然深爱西西里,也对“粗俗的村民们怀有兄弟般的感情”。一旦革命来临,“城市和橘园在这派景色中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华丽饰物”,而“干旱的、荒芜的、不合情理的圆形山丘此起彼伏,以至无尽”,故乡的未来陷入迷途,他又表现出深刻的无可奈何,总是为西西里发出无尽的叹息。
“我是一个可怜而软弱的男人”
亲王的叹息既源自对西西里历史与未来的拳拳之心,又源自对自身及家族命运的乡土深情。作为旧势力的代表,深处变革的大潮之中,亲王无论面对谁、面对什么都踌躇迟疑,在反反复复的思考和不确定中拉扯。这导致亲王对待革命的态度相当暧昧,在多纳富伽塔期间,统一的意大利宣布诞生,他既能感受到“任何其他的形式都不如这种形式”,又觉得“干巴巴宣布投票数字以及过于哗众取宠的言说中,一定有着什么,或者什么人死去了”,其矛盾的内心可见一斑。
一方面,身为贵族,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亲王都秉持了若干年来养成的阶层传统,葆有阶层的高傲甚至傲慢的原始本能,即便面对新政府的官员也要装扮出“一点浩然气”:“我代表旧的阶级,不可避免地和波旁王朝有牵连,由于情面的关系,而不是感情的关系,和它联系在一起了。我属于不行的一代,它介于新老两个时代之间,因此,跟其中的哪一个时代也不合适”,也因此,他“慷慨激昂”地拒绝了谢瓦莱的邀请,看上去极为“洁身自爱”。其“底气”既来自作为贵族阶层的惯性,又来自他身处其中所需要的浮华和虚荣。
另一方面,如亲王所思,“王国(两西西里王国)的根本利益,本阶级的利益,以及他私人的利益,统统在那些虽有创伤但仍保留一定生命力的事件中消失了”,实际上他也深知,西西里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巴勒莫贵族必将走到历史的暗角。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作者单独以一章介绍亲王病逝近20年之后萨利纳的家族生活,虽物是却人非,家族的女丁显然支撑不起曾经的“贵气”,想必这些都在亲王的预料之中,所以活着的时候,他才会若有所思、长夜难眠,未尝不叹息于王朝的背影。总之,骨子里的卑微和举止上的高傲塑造了亲王对革命或变革相当茫然的态度。
那么,作为西西里贵族领袖,亲王的立场应该或者需要是什么呢?纵观从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欧洲各国革命中的贵族,复辟者有之,沉寂者有之,消亡者亦有之,最终都纷纷走下历史的舞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亲王似乎已经深谙其道,也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一句“我是一个可怜而软弱的男人”,似诉平生不得志,所谓“可怜”,意指境遇之艰,所谓“软弱”,慨叹选择之难。从历史的维度看,也正是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在革命风雨中保全了亲王及其家族。
“舞厅里,人们看到的都是金子”
虽然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是当年的舞榭歌台依然在这部小说中泛溢如泉涌。《豹》中《舞会》一章无疑是整部小说的高潮,也是小说关于1860年代的收尾章,兰佩杜萨在有限的空间内调动了几乎所有的小说人物,在众声喧哗中还原出一个家族最后的“荣光”,而且用了大量的笔墨言说舞厅之奢华:“舞厅里,人们看到的都是金子”,金光闪耀、豪华富丽,使那里“浮华虚荣的男男女女”充满“肉欲的激情”,进而将整部小说的“巴洛克”风格推向极致。
意大利最不缺少“巴洛克”,17世纪之后巴洛克建筑风靡半岛,奠定了世界巴洛克建筑的基础,同时又使作为美学原则或概念的“巴洛克”跨媒介远及雕塑、绘画、文学领域。虽然巴勒莫是一个以阿拉伯-诺曼为主要风格的多元建筑城市,但是其巴洛克风格显然成为兰佩杜萨的起点。早在第一章介绍亲王家族时,他就不惜笔墨,描摹萨利纳家族府邸的金碧辉煌以及其间具有矫饰风格的陈设和布置,并直接指出,“每个封地都喜气洋洋,都想直接地或间接地颂扬萨利纳家族的开明的权力”,极力刻画家族背后的“权力”。
如果说在建筑、装饰、衣着上是巴洛克风格的自然流淌,那么在《豹》中兰佩杜萨将巴洛克运用到一些细节则昭示出他的写作策略。萨利纳家晚餐的排场、关于家族封地的巨幅油画、亲王普鲁斯特式的内心世界、青年男女坠入爱河、采药人和神父的秉烛夜谈,都被作者做了巴洛克式的“动态”处理,一些场景堪称极端。比如亲王出浴的场景,他“浑身冒着热气”,“水顺着他的脖子、手臂、胸口、大腿往下淌着,宛如一条条溪流,就好像罗纳河、莱茵河、多瑙河、阿迪杰河穿过并滋润着阿尔卑斯山区一样”,其中的跃动和复杂显然已经出离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表述。
然而与文艺复兴后期的巴洛克文学不同的是,兰佩杜萨即便在塑造巴洛克,也并没有打破20世纪下半叶意大利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学准则,他不是错彩镂金地雕饰语言或塑造情景,而是在“巴洛克”背后塑造一种静穆的“有用”:作为形式和内容的“巴洛克”都是一种易冷烟花的象征,以至于作者在极力描写封地之美后不无遗憾地言明,“上述的一些封地,虽说在画面上欣欣向荣,实际上却已经飞逝,只不过在五彩缤纷的画布上和在名义上留下痕迹”,显然也意在说明,古老的奢靡和矫情早已灰飞烟灭,所存留者无非烟云而已。巴洛克,成为家族没落的回光返照。
兰佩杜萨的“晚期”风格
回光之一,当然是“豹”。作为具象物的豹是萨利纳家族的图腾,会出现在从巴勒莫到多纳富伽塔的诸多家族建筑物上,“挺立在府邸和大教堂的门面上方,出现在那些巴洛克式的喷水泉顶端,就是在他们自己房屋里的陶制贴砖上也可以见到”。作为抽象物的豹,则是家族权势和威严的象征,而曾经的亲王“身材高大魁梧,体格异常健壮”,俨然是“豹”的人间肉身。之所以强调“曾经”,盖因小说中“豹”并非永远如亲王一样魁梧健壮,在生命的末期,他已经成为“一只孱弱的豹”,来到萨义德意义上的“晚期”。
“晚期”是一种风格,也是这种风格在小说文本中的投射,集中表现在对亲王的塑造上,基于晚期风格,兰佩杜萨为亲王形象注入了无边无际的“世纪末”情绪,以至于将其中一章命名为《亲王的烦恼》。其实除了对西西里过去、现在、未来的担忧,他尚有诸多其他烦恼。烦恼之一是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常常失眠,深感年龄带来的体力不支,甚至已经开始对年轻人的爱情存在某种“肉欲的妒忌”;烦恼之二是受此影响对过往的眷恋惆怅与“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矛盾,越是暮年就越感受到岁月的流逝,亲王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长久伫立目视远方,正是矛盾的文本体现;烦恼之三是生命的归宿与西西里的归处在亲王内心事实上已经合二为一,一旦将两种“未来”融为一体,亲王的思考就会变得愈发沉重,愈发“晚期”。
就亲王形象而言,“晚期”的极端自然是死亡,所以兰佩杜萨专门写了《亲王之死》一章。亲王去世于1883年,距他出场的1860年已有23年,读者不知道这23年里巴勒莫和西西里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亲王深感生命之流不停地在体内消逝,仿佛已经张开翅膀飞向上帝:他结束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凄惨的”“像葬礼一样缓慢的”旅行,感受到“离他而去的时间仍然风驰电掣般地在消逝”,最后终于死在了众人的目光里。速死,是亲王留给读者的文本错觉,一旦考虑到“晚期”在23年间对亲王的折磨,速死便既是“晚期”的结果,又是亲王的解脱。
更重要的是,小说中亲王的“晚期”,跃出文本也就成为了作者兰佩杜萨的“晚期”,毕竟写完《豹》的1957年,他已值暮年。天涯孤旅、酷爱文学、草木一秋,共同塑造了他的一生,而历史的沉思、文学的积淀、家族的深情使其在生命的尽头用心完成一部杰作,这部杰作也几乎成为他在现实横轴和家族纵轴的投射。虽然亲王的原型是兰佩杜萨的祖父,但是不难推断,作者在小说的镜像中也可以真真切切地看见他自己。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如萨义德所言,兰佩杜萨的“晚期”具有一种非常令人信服的本真和一种强硬的苦行原则,排除了多愁善感的怀旧。
“假如我们希望一切如故”
当然,作为沉郁顿挫的作者,兰佩杜萨对小说及历史的思考远远不止于此。作为贵族的后裔尤其是小说主人公原型的后裔,他必然在《豹》中循循唤出如《我幼年待过的地方》般诸多关于童年的记忆或创伤,这部小说也一定充溢着兰佩杜萨若干年来的文本想象或历史想象,寄托着他的历史观念。在小说隐秘的纵深处,作者经由其中各式各样的人物或形象思考各个阶层或阶级对加里波第登陆的现实和历史态度:对于采药人来说,新政府给予他们的是赋税的威胁;对于彼罗内神父来说,他需要为了维护萨利纳家族的尊严描绘一幅黯淡的未来图景。事实上,大家对革命的态度都暧昧不清,这也是采药人不停追问神父萨利纳亲王到底如何看待革命的原因。
遗憾的是,彼罗内神父的答案是:“他说并不存在任何革命,一切继续如此”,表面上看似乎暗示着亲王对革命的否定态度,实际上却是一个连采药人都嗤之以鼻的答案,也从侧面凸显出了亲王对待革命的茫然和无能为力。比之于“传统”的亲王,“现代”的唐克雷迪在革命面前略显高明,他一出场便说出了《豹》中那句著名的箴言:“如果希望一切如故,就必须改变一切”,这句话揭示了唐克雷迪的实用主义态度。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先是加入红衫军,后又背叛了加里波第成为撒丁王国的军官,投机且钻营,却迎来了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同时,这句话也反映了年轻的唐克雷迪对历史变迁和权力更迭的深刻反思,颇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可然律思考。而比之于政治情节和历史故事,唐克雷迪与安琪莉卡爱情的文本意义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这样一来,兰佩杜萨就用唐克雷迪的“一语中的”解决了亲王的“优柔寡断”的问题。跳出文本,生活在1860-1880年代的亲王和唐克雷迪,与时代尚未产生“时间距离”,所以很难形成关于历史的观念,但兰佩杜萨却可以将他们这种缺失“转嫁”到自己身上,使二人共同形塑作者的历史观念。实际上,在《豹》中,作为作者的兰佩杜萨成为被分成两半的公爵,法布里契奥亲王和唐克雷迪分别承担了他无论是灵魂还是肉身的一体两面,以答解问,在不知不觉间告诉读者,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不会因任何人的留恋而改变流向,我们只能适应它。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然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处于创作中的兰佩杜萨也必然会将《豹》中言说的历史及其家族的百年兴衰与1950年代的意大利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巴黎和约》和“马歇尔计划”签署以及国内政治逐渐清明,意大利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迎来了一个经济的高速增长期,直接改变了意大利人的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加之早在“二战”结束之后,意大利就开始解决南方问题,“南方”伴随着这一轮经济腾飞而崛起,泛起许多涟漪。兰佩杜萨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在新社会和旧贵族的对比中,他也一定能够感受到世界潮流的浩荡,以至于在《豹》中只呈现悲观主义本身,却不对任何历史事件或现象进行明确的评价。然而无论如何,他都在一个意大利社会的繁荣期创作出了一部重要的小说。
遗憾的是,写完这部小说的1957年,夏风吹落了杏树的花瓣,也吹落了兰佩杜萨,他终未见到《豹》的出版。要不是小说家乔尔乔·巴萨尼慧眼识君,力荐出版,恐怕这部小说还尘封在历史的褶皱之中,读者也不会了解到兰佩杜萨姓甚名谁。虽然福斯特说“豹子不会屈居于草莽之中”,然而兰佩杜萨终究是死了。尽管逝水不归,落花亦不再返枝,但意大利文学史上能留下这样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杰作,我们也应该满足了。
(作者系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