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桑梓
诗人陈年喜没有被出名所改变。在前作《炸裂志》《微尘》被更多人读到后,他的名字出现在许多媒体的报道里。在媒体的采写中,他与王计兵、余秀华等同时代走红的创作者常常并列,作为打工诗人或“野生写作者”的代表。但与刻板印象不同的是,陈年喜的写作并不等同于苦难叙事,也不是迎合某种身份的媚俗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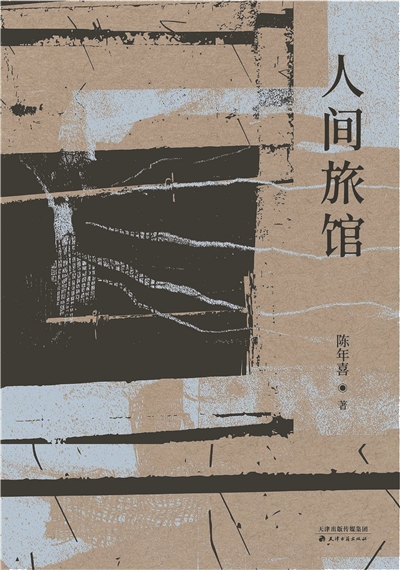
大地上的漂泊打工者书写
他是一个本分、耐心、贴着经验去写,又有些苦吟派滋味的写作者。他的写作技巧并不时髦,无论是语言本身,还是叙事方式,都更像是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但他在写作中不回避现实的坚硬成分,采用正面强攻的姿态,这比炫技本身吸引来了更多的读者。他们从陈年喜的作品读到生活,读到自己,读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社会。说到底,真诚仍是陈年喜取信于读者的核心要素。
许多读者对诗人陈年喜的认识,是从《炸裂志》这本诗集开始,矿山、皮村、秦岭、北京、大雪。陈年喜用153首诗歌,浓缩了一位创作者与劳动者对于尘世的思索。在诗歌之外,陈年喜的另一个主要创作领域就是非虚构。《微尘》《活着就是冲天一喊》与最新出版的《人间旅馆》都是非虚构题材。
他的非虚构作品常发布在“人间theLivings”“澎湃湃客”“真实故事计划”等非虚构平台,由于公众号篇幅与平台的潜在影响,他的部分非虚构稿件具有明显的媒体腔。反而是他更新在自己的账号,或者不以强戏剧冲突、热点选题为要素的文字里,流淌着更加个人化的东西。
我曾根据自己的阅读范围,将陈年喜的非虚构创作分为三类。
其一,是以叙事者“我”的亲历为故事来源的回忆型写作;其二,是具有类似媒体采写气息,用叙事者“我”的调查与纪实串联起来的写作;其三,是具有散文气息,更富有风格化、作者个性化的写作。
在新书《人间旅馆》中,陈年喜书写的主体是大地上的漂泊打工者。全书分为三部分,共十九篇,其中既有陈年喜对矿工生涯时认识的各色人物的书写,也有他以黄栌、橡子树、年戏、苦荞等自然或文化元素展开的回忆。
在自序中,他自陈“我这半生,与漂泊有关……作为行走求生计的人,几十年来以及今天,我总是在和旅馆打着交道,进矿前,下山后,所有来来去去的赶赴中。”旅馆是他串起漂泊生活的载体,也是一个远行人相逢的中介。
延续《微尘》等前作的基调,陈年喜继续书写一个在北上广深之外,更接近大部分中国劳动者生存状态的世界。作者以记录者和亲历者的视角,呈现了矿工、马夫、淘金客、客栈主人、县城女人的多元世相。譬如:计划去喀喇昆仑山找玉的人,他们带着干粮和帐篷,沿叶尔羌河往上走,据说翻过山就是阿富汗;在山脚的岩石上打孔的工人,用炸药炸出一条便路,多年前,工人住过三块钱一晚的旅店,为省电,老板不让拉灯,上厕所看不见,需要点一支烟。
一部绵延的工作志
吹唢呐、打铁、炸山、淘金、开旅店……一部《人间旅馆》堪称一部绵延的工作志。陈年喜在书写矿工生活时,采用符合人物特质的对话、大量精准的生活细节,给予了读者一种可信的亲历感。
例如《深山旅店》一篇,工头带着叙事者“我”和张锁上山去选洞址,三人带了一柄大锤、两根钢钎、几包炸药,陈年喜写三人对话。张锁:“这是上天,哪是上山。”我:“不行,路上力气都耗光了,到了地方也干不动活儿了。”工头:“那就找个人,帮我们背脚。”像这样的对话,看起来没什么文采,其实是很实的,这样的对话累积起来,人物的真实感才有支撑。
也是在这篇里,有一个细节体现出陈年喜是在贴着人物写,而不是概括人物。这个细节出现在三人第一次见到开深山旅店的店主毛子时,作者是这样写的:“来人是一个中年,也许是青年,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刮过脸了,胡子占据了三分之二的脸面……”如果是概括型的口吻,一般作者会直接写“来人是中年”,而不会有后面表示猜测的口吻。陈年喜这样写,会让读者更能够感到他们是在随着作者,身临其境地体验一次探险之旅,而不只是干瘪瘪的概括。
整篇《深山旅店》,其实就是围绕着毛子在写,写“我”和他的交集,写这家深山旅店背后不平凡的故事。这篇作品里,有一个看似闲笔的细节用得很妙。
作者写矿坑坑口东边,“有两棵巨大的黄栌,像两兄弟,都有合抱粗。秋天的秦岭层林尽染,气象万千,但都以黄绿为主,唯有两棵黄栌的叶子是红色的……像两堆火焰。”有一回,毛子坐在黄栌树下吃烧鸡,红叶落下,他捡起叶子看了看,突然说:“要是将来能睡这两棵树,该是多好的事呀。”
后来,毛子走了,去县医院查,回来后一个多月就不行了。那两棵挂着红叶的黄栌,在他死后成了棺材所需的木料。
新作中的不足与变化
相比起《微尘》,陈年喜在《人间旅馆》里的笔触更克制。书中有不少情节,如果爽文写手去写,很可能变成故事会或者控诉体,但陈年喜选择避开浓厚的抒情。
陈年喜还善于将历史与今天发生的、两件看起来毫无关系的事情结合来写,产生有趣的叙事效果。比如散文《阿哈,塔巴馕》:“曾听采矿工程部的老李头说,几千年前这里很繁华,匈奴、塞种、乌孙在这里打杀,生死,闹花灯一样。但那都是历史了,与今天无关,也与我们无关。我们找了家不起眼的小旅馆住下来,三个人要了一个大间,加上位置偏僻,讨价还价一番,算下来省了不少钱。”
陈年喜的文字有民间味、生活感,因为他善于将地道的、民间的表达融入在比喻和对话里。比如写友人睡觉,他说是“羊膻味的鼾声”;写新疆的星星,他说“满天的星星杂乱无章,像翻了一地的花生,地太肥了,花生一颗颗都长爆了”;写四川朋友小邹对新疆星空的感慨:“看人家新疆的星星才叫星星,我们四川那叫啥鸡娃子星星!”
读《人间旅馆》,我的另一个感觉是,陈年喜写结尾时更淡然了。在典型的类型化故事里,作者会在结尾里给读者一个明确的交代,比如英雄获胜、反派死去、荒诞之事落下帷幕。读者经常看到一个象征故事完成了闭环的收尾,或者欧·亨利小说那样的反转。在《人间旅馆》里,陈年喜写的结尾更像是淡淡的暂停,像一个中年人在古树下聊天,讲着讲着,到了饭点,就先抽身。
故事收尾不再激烈,也不必有所升华,但更符合人生的况味。
最后,若说这本书的不足,笔者以为有两点较为明显:其一,作者虽然把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但这三个部分区分度并不大,结构上的层次感并未得到很好的建立。其二,书中有一些篇目有凑数之嫌。譬如相比起《深山旅店》《老四》《缝衣记》,《忆黄土塬》《感冒记》就显得浮泛,没有把要写的东西很好地展开。
这本书的不足,陈年喜在序言中也提到:“但要记录他们,也并非易事,因为我也是匆匆过客,萍水相逢,擦肩而过。所以这些文字,并不深入和完整,它像电影镜头,远观或拉近,多为匆匆一瞥。”当然,这段话也有作者自谦的成分。散文写作,或遣悲怀,或发幽思,或写人状物,或描梦言志。散文之于陈年喜,既是他对自我生命的提炼,也是他让一个个无名者个体生命展开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写作继承的是“文以载道”的传统,但与其说是说教,不如说是唤起和提醒,提醒人们,这个世界还有这些血肉充沛的生活。(桑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