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周广玲
作家王威廉的随笔集《我见过那个人》以“人像”作为棱镜,巧妙地折射出人性光谱中最为隐秘的明暗之处。这位兼具物理学与人类学背景的作家,手持文学这一精密的显微镜,将街头巷尾的陌生人、历史尘埃里的显赫人物以及亲密圈层中的同行者,逐个放置在观察台上,精准地剖析出生命最为本真的内在肌理。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场畅快淋漓的人性速写,更是一次对文学本质的深刻哲学叩问——在人工智能逐渐侵蚀表达空间的当下,灵魂的深度究竟如何成为文学最后的指引灯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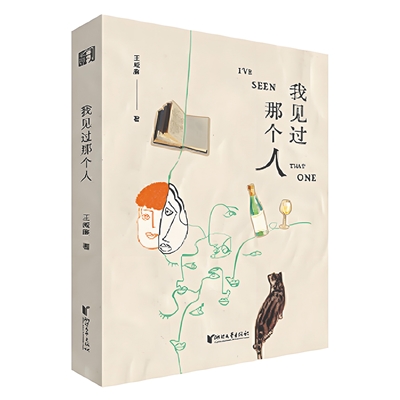
书中开篇之作《我见过一个人》,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于“看见”的常规认知。王威廉笔下的“见”,绝非简单的视网膜物理成像,而是“对事物的理解和记忆”所呈现出的精神显影。他所捕捉的人物宛如浮世绘中的众生百态:麦当劳里与服务生发生争执的女人、天后宫中静坐的老妪、从朝鲜战争归来的伤残老兵……这些在日常目光中被轻易筛落的“透明人”,在他的文字世界里获得了如青铜般厚重的质感。
尤为令人震撼的是他对边缘人物的凝视逻辑。与波德莱尔对“恶之美”的展示不同,王威廉尝试在乞丐身上发掘出“古希腊哲学家的独特风采”,在商场售货员机械重复的动作里,探寻“社会机制所锻造的惊人忍耐力”。这种独特视角源于一种谦卑的共情心理,他坚信,每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外表之下,皆是灵魂精心伪装的外衣,而文学的使命便是刺破这层伪装,让陌生人的生命经历成为我们自我认知的一面镜子。
物理学的专业训练,为王威廉的观察赋予了精确的坐标体系。当描写一位流浪者时,他会将个体放置于“人类历史空间”的宏大网格之中:从横向角度扫描其与社会机制之间的碰撞与互动,从纵向维度追溯历史基因在其身上留下的深刻烙印。而人类学的广阔视野,让他能够摒弃学科偏见,始终以“整体性视野”深入剖析人性。
这种跨维度的透视手法,在《鲁迅的目光》一文中达到了极致。当鲁迅在梦境中以“和煦温柔”的崭新形象,取代了教科书中一贯冷峻的面孔时,王威廉完成了一场对历史人物的精神抚慰。他穿透岁月的重重岩层,真切地触摸到鲁迅作为“人”而非单纯“符号”的温暖。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实际上是作者对文学本质的深刻隐喻: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让逝者在文字的血脉中重新焕发生命活力。
书中对于科技与人文关系的深入思考,发人深省、振聋发聩。当ChatGPT能够编织出精巧绝伦的故事时,王威廉犀利地提出疑问:“魔术师般的语言组合倘若远离灵魂的深度,还能够被称为文学吗?”他深刻地揭示了人工智能的致命缺陷——它永远不会因生命的虚无而感到痛苦,也不会在深夜被创作的冲动所深深灼伤。
《我见过那个人》最终指向一种“出窍”的生存哲学。所谓“出窍”,并非脱离现实世界,而是如王威廉所说:“在清醒理智的状态下拓展思想的广阔疆域,构建一个平行于日常生活的精神世界。”书中每一个被精心书写的人物,都是作者投射自我的生动镜像:流浪者体现了他对自由的热切渴慕,监狱诗人映照出创作过程中的艰难困苦,西施与荆轲则折射出历史暴力对个体的无情伤害。
这部随笔集因此成为一部珍贵的灵魂备忘录。当算法试图将人性简化为冰冷的数据,王威廉用充满温度的文字捍卫着生命的不可解析性。那些眼泪的温热、颤抖的双手、欲言又止的沉默,共同标记着人之为人的独特坐标。在速写陌生人脸庞的刹那,他完成了对时代最为温柔的抵抗:让每一个渺小的生命,都能在文学的世界里获得尊严的栖息之所。(周广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