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王津京
发表于1991年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被认为是20世纪80、90年代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同时期还有黄建新的《背靠背,脸对脸》等一系列电影作品。孟京辉2001年拍摄的电影《像鸡毛一样飞》虽然带着鲜明的浪漫色彩,但主题也同样在讨论当代人追逐利益、财富的同时面临的精神危机,尊严、情感、正义感的缺失引人警惕。
近日上演的独角戏《一地鸡毛》,结束在主角小林弯腰要拾起一根鸡毛的时刻。灯光骤灭,观众都为演员张一山松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休息了。110分钟的独角戏,他要爬高钻桌,不断换装,不时推动占满舞台的折叠镜墙,虽然没有特别高强度的肢体动作,但大量的台词、15个角色身份,也足以让演员精疲力竭。当年的小刘星如今已经成了大明星,20多年的演艺道路上,他也经历了一些起落。33岁的他将如何演绎一个小职员的心路历程?那拾不起的鸡毛,抑或是那弯腰伸手的动作代表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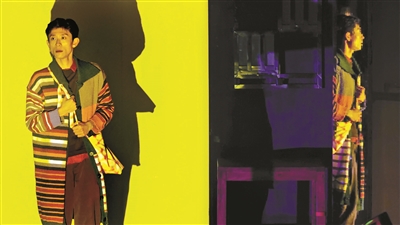
独角戏《一地鸡毛》 摄影/塔苏
熟悉的“一地鸡毛”,被期待的独角戏
即使没有看过小说原著和电视剧,大家也都知道“一地鸡毛”这个词语。小说《一地鸡毛》以对改革开放初期职员小林工作与生活的细致描写,以及他做的一个躺在鸡毛堆上的梦,将“一地鸡毛”引申为生活琐碎、窘迫之义,一种纠结、拧巴继而妥协的人生境遇由此有了一个经典代名词。
熟悉原著和电视剧的观众则可能会对话剧舞台的呈现有一些期待。首先,原著中那些琐碎但可见微知著的事件和情绪如何展现?比如小林上班迟到如何辩解?面对妻子的抱怨如何反应?与远道而来、有恩于己的老师如何惜别?老婆换工作求人,连礼都送不出去是怎样的尴尬?要放下尊严体面去抛头露面卖板鸭,又是怎样的犹豫?伴随这些经历所产生的情绪,在相对写实的电视剧中没有被放大,但在舞台上应当有更鲜明的表现。
其次,话剧改编在主题上会有怎样的突破?可以想见,舞台上必定有鸡毛撒落的场面,但小说中被瞬间遗忘的梦境如何在话剧中升华?
最后,既然是独角戏,演员对角色转换的处理自然备受关注,包括对演员能力的期待,以及在表演环节如何展现小林对生活和自我的反思。
尊严逐步让位置换“完满”生活
本剧的创作者丰富了小林的生活细节,突出了他的内心活动,以或诗意或有哲理的语言将原著中的事件引向更深层面。全剧开场基本沿用了电视剧版的情节,刚进单位的小林因为正跟女友打得火热,经常迟到。“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影响谁?大不了我晚走5分钟、10分钟。我,一个小科员,能影响谁?”不到300字的独白,干净利落,将小林的基本情况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清晰展现。
接着便由他的迟到转入刻画其如何逃避责备,电视剧中的小林在院子里跑步,在话剧中这一行动被加上了几句貌似积极的豪言壮语。进屋后,小林一遍又一遍地放皮包、拿水杯、磕磕文件夹,甚至钻到桌下,对观众表示“好像没糊弄过去”。然后,演员开始演绎单位的众生相:要升官的领导老张、爱管人的女老乔、任性自我的女小彭、生活艰难的老何和安排“正经事儿”——聚餐的老孙,演员给每个角色都设计了一种固定的动作姿态。这里要肯定演员对人物语言的处理,在不夸张发音也不使用方言的情况下,仍能够将人物清晰地区分开。
小林与李静交往结婚的过程是令人愉悦的,演员在两个角色之间的切换行云流水,相比其他女性角色,对李静的处理在姿态和语气上更加克制。结婚生子,人之常情,但合租房的生活成为“一地鸡毛”的开始。厨房、厕所都成了争夺的战场,小林着急忙慌地择菜、洗菜、烧油、炒菜,激烈的动作和“只要我炒得快,谁也赶不上我”的局促魔怔状态,积聚着生活的负累感。终于,他想到工作了20年还一家六口挤在15平方米里的老何,感到自己必须跟领导老张要求换房。正好老张升官搬家,一众同事来帮忙,他尽献殷勤,连厕所都帮忙刷洗,但心里仍然觉得既无底气也无时机。最后还是因为老张搬家,带动一系列人换房,小林才换进了老何那15平方米的房子里,不知道是不是刷厕所刷出了运气。
由于拆迁,小林一家又搬进有独立厨房、卫生间的周转房,还请了保姆照看孩子,生活前所未有地完满。但下一轮的“鸡毛生活”很快又开启了:换工作、接待老家客人、辞退保姆、送孩子进幼儿园、给幼儿园老师送礼、卖板鸭,直到收下查水表老头送来的微波炉,吃上了微波炉烤肉。什么蹭领导为小姨子增设的班车、什么给隔壁孩子陪读,都不算什么,生活似乎终于幸福起来了。
人物的选择背后,应有创作者的态度
话剧在原著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情节和解释,展现了小林如何在马不停蹄的生活中变得麻木,甚至遗忘了真善美。
首先是“凉鞋理论”。这让人想起黄纪苏编剧、张广天导演的话剧《切·格瓦拉》,用一种很理性的方式从某物的产生和物理意义说起,从凉鞋是怎么回事落到他如何接受了上班不能穿凉鞋的规定。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小林必须遵守规矩,也需要曲意逢迎,一个“愣头青”就这样在人情社会里变成了“老油条”。
此外,话剧用独立的场次对小林大学时的状态进行表现。舞台设计为上下两层,上层左侧是小林大学时的场景:那时他的大学同学“小李白”才华洋溢,小林也满怀诗情,李静也能在信中写道:“意缱绻,惹人徘徊,盼期末考后,晤面长谈。”但诗情画意终究抵不住生活的压力,人也就遗忘了美。舞台上层右侧则是卖起板鸭的“小李白”的表演段落,他说:“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浑扯淡!”而李静也从那个文静的姑娘变成了满腹牢骚的妇人。
还有在与杜老师惜别时,小林看到挤公交车的人群。这里编剧使用了诗意的语言,“人,人,人,一个挤一个,一个挤好几个,所有人挤着所有人……”满脸皱纹、驼背的老师在其中,向小林微笑着挥手。在原著中,所有的事件和人都是让小林向下坠落的力量,只有杜老师是一抹亮色。“发生了什么?什么发生了?”此处小林的良知闪现,但最后仍被生活淹没。编剧在这里的设计应当是试图放大这一事件对小林的影响,但舞台呈现对这一段没有进行特别的处理,演员对这一段话的演绎也欠缺深度。
小林卖板鸭时抓住了一个用假币的女人,他从那一抓中感到了某种兴奋。以前自认没钱没门路的小林,在挣了钱后就硬气起来了。似乎那一抓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尊严、抓住了勇气,即使被同事老孙发现自己卖鸭子也不怕了。
1991年,梁左创作的相声《着急》由姜昆和唐杰忠在春节晚会上演出:同样是小职员的老纪从早到晚、从年轻到年老,为生活、为工作、为孩子着急了一辈子。囤蜂窝煤、囤大白菜、囤副食品,那个时代的普通人都是如此。《着急》指出了大家共同的问题,大家笑老纪也在笑自己。话剧《一地鸡毛》中,小林和李静没能送出去的可乐被小林自己喝了,这个场面多少令人感到一些自嘲的力量。
但最终对于穷着还是要过得好的选择,表达似有不妥。这不是两个平等的选项,而关乎是否要为了烧鸡啤酒抛弃自尊、堕入庸俗。如果小林将两者视为平等,而选择要更好的物质生活,那么创作者就要批判这一选择。那拾不起的尊严与道德良知应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最后的场面应当含有创作者的态度。
其实全剧都存在这个问题,即小林以何种态度回忆或陈述自己的经历?每一个事件对他的影响到底是什么?缺失这个基本态度,也就缺失了情绪起伏的基础,这是全剧节奏平淡的根本原因。小林应当从那一地鸡毛中站起来,发现老师已去世,面前摆着烧鸡啤酒,突然感到了些什么,带着一种疑虑的心态从过往寻找答案。即使最后仍然选择顺从生活,也要让观众感到那无奈的悲凉。(王津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