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蒋柳凝
自《卢克明的偷偷一笑》(下文简称《卢克明》)发表以来,不少读者表示,他们难以按照余华期待的那样“从头笑到尾”,“即使有眼泪,也是笑出来的眼泪”。我们为何对卢克明的“偷偷一笑”难以感同身受呢?或许是余华揭露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些令人不安的真相,又或许是余华这一次的喜剧写作本身存在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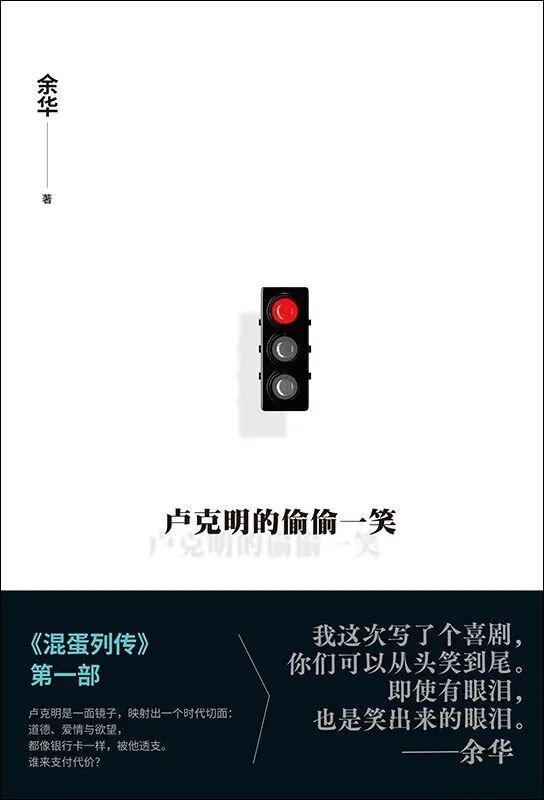
《卢克明的偷偷一笑》余华 新星出版社 2025.12(图片源于豆瓣)
从《活着》到《第七天》《文城》,余华的小说一贯以“悲情传统”“苦难叙事”著称,但《卢克明》则打破了这种叙事惯性,转而以夸张、戏谑的喜剧笔触讲述了一个“混蛋”的情场往事与商海沉浮。这体现了余华对喜剧艺术的创新追求,但也暴露了他对欲望喜剧的误解。
《卢克明的偷偷一笑》是余华“混蛋列传”系列的开篇。小说的主人公卢克明是一个纵情声色、油滑狡黠、攀权附势、冷酷算计,又不乏一些人情味的家装公司老板。这个人物虽令人反感,却无法让人厌恶得彻底。他是如此成功且自洽,非但没有在欲望中走向虚妄,反倒因对欲望的追逐与放纵而过上了美满的人生。卢克明这个角色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兄弟》中的李光头,他们的身上都深深烙印着市场经济时代蓬勃的物质欲与精神欲(主要体现为色欲)。比如《兄弟》中写李光头举办“处美人大赛”,满足自己的窥私欲,大行敛财之实,最终却在膨胀的欲望中陷入虚无。在欲望的“满足——幻灭”这一自反性结构中,小说的批判性得以实现:在欲望的虚无本质上映照出人类存在本身的荒诞。反观《卢克明》,我们在其中看不到作家对欲望的本质性解构。“卢克明”式的混蛋们以超出善良、有原则的人们所能想象的方式快活地存在。小说的批判力度似乎大大被减弱了。

《活着》余华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7(图片源于豆瓣)
喜剧的结局往往决定着喜剧的调性,为何要给卢克明安排这样的结局?按照余华的说法,如果给卢克明一个悲惨的结局,既轻易又廉价,反而是“软着陆”的结果才真正具有批判性。这种与90年代新写实相似的“原生态”写法,旨在真实呈现生活中存在的那类无视道德与秩序的“混蛋”,以及孕育这类人的社会历史语境,并且借由世界本质的无序与荒诞,揭示道德叙事遮蔽下某些令人不安的真相。
为了达到理想的叙事效果,余华进行了一次不同于以往的大胆实验:在保留过去那种粗糙、直白且毫无克制的个人风格外,隐去了叙事者所有的技法,进而形成了一种去除深度模式、取消小说意义表达的后现代叙事。当叙事者以零度、先验的姿态隐匿,赤裸还原欲望社会,那些莫名的结局、零碎的情节与扁平的人物,反而取代了本该精心营构的喜剧结构,以及对欲望的哲学性演绎。由此可见,余华对欲望喜剧的误读,根源在于他对喜剧这一文体存在认知偏差。他误以为,借助一种取消小说意义深度的后现代式的叙事,就能更好地展现欲望喜剧的讽刺性与荒诞性。一旦选择了这种反常规的叙事,无疑便忽略了喜剧的本质——“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导致这部小说必然缺乏欲望喜剧该有的价值判断,以及社会批判的力度与深度。
不得不承认,余华的叙事经验正在逐渐凸显出其局限性。自《兄弟》以来,余华似乎很难准确地把握过去那种行之有效的叙事姿态。例如,他的写作多半由现实题材出发,试图借助新闻有效深入现实,却总是无法在小说的艺术质感与新闻的纪实属性之间寻得平衡。在小说中植入新闻,理论上是为了让文学文本成为现实问题的载体,履行文学的社会批判与人性深探的职能。《第七天》中对新闻“串烧式”的罗列曾遭人诟病,其以牺牲小说艺术性为代价,借大量新闻推动情节发展,粗暴且直观地连接了现实与虚构,在直面种种悲情与苦难的过程中给人以强烈冲击。《卢克明》则借新闻标题内在的戏剧性与小说情节的前后反转,瓦解了新闻的严肃性及其意义。如“嫖娼者自己报警,警方端掉色情窝点”的新闻,在小说里变成网红博取流量的营销密码,被塑造成新媒体时代娱乐化、刻奇化产物的存在,这再度实现了“去除深度模式”的叙述,无疑又陷入了“主题先行”、新闻移植目的性过强的窠臼之中。
余华的实验还体现在对话语的革新,正试图挣脱那种以文学性、艺术性为内部架构的“纯文学”话语。话语的反叛突出体现在人物有关性话语、政治话语的对白中。小说中,许多严肃表达已经完全脱离原有涵义,被肆意曲解为性话语。性话语已不像在《兄弟》中那样作为次要元素出现,一跃成为小说主要的话语模式。当叙事者隐退幕后,卢克明式的“混蛋”们在文学话语的失范中,以肆无忌惮且带有强烈性暗示的语言占据了文本的叙事空间,令小说的叙述显得粗糙、裸露而略显低俗,给人带来一种浅表性的、深度受限的阅读体验。尽管这是“卢克明”的幽默,而非余华的幽默,但作家也难辞其咎。
《卢克明》展现了余华对喜剧艺术的创新性追求,这一点值得肯定。但作家对固有的语言系统及意义模式的大胆反叛与刻意混淆,在带来轻松的喜剧效果的同时,也引发了文本内容趋于单一、意义流于平面的焦虑。从《兄弟》到《卢克明》,余华在艺术呈现上的某些不足,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当下普遍的文学症候:作家试图有效介入现实,却找不到合适的方式;作家试图在形式策略上有所创新,却又难以抵御叙事惯性。所以,《卢克明》便只能呈现出这样的效果,令人有所期待,却难以使人满意。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