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史静 范楷
文学作品中的乡村叙事,通常是由经度和维度构成的。今年8月,莫言的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将乡村叙事的时间法术用到了极致。书里的乡村是在回忆中呈现的,乡村时间和物候联系为一个有机整体,而时间预叙又让乡村叙事超越了现实性,有了一种超越性。最终,建构了在当下语境中乡村的审美意识形态,以及乡愁的别样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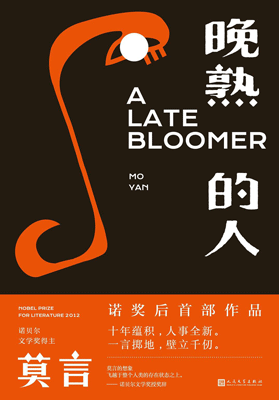
时间回忆术
《晚熟的人》中,最强的时间结构相似性在于,故乡是在叙述者“我”的回忆里呈现的。“我”在编织乡土叙事的经纬线时,纬线往往是固定的,就在故乡高密;经线则是不固定的,最主要的特征是每篇小说中故乡的人和事都在回忆中展开。
在整本小说集中,不时会出现“我经常回忆起”“我记得”“我经常梦到”“那时候”“那时”等一些时间语法结构,而且主要在段落开头出现,从而引出一段故事、几个人物。例如,“我经常回忆起那个炎热的下午,那时候田奎还是一个双手健全的少年”“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经常梦到在村头的大柳树下看打铁的情景”等。正如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追忆叙事手法,追忆是一种建构叙事的时间滤镜,有了这层滤镜,更容易将记忆中的现实温情化和复杂化。
《晚熟的人》里的小说,往往以“那时候”开头。例如,《斗士》中写道,“那时候冬天很冷,夏天很热。那时候夏天的中午,村子里的男人,不论老少,都泡到河里”等。叙述者“我”回到家乡去观察,使每篇小说中的人物有了历史的深度,超越了简单的善与恶,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吊诡性。因为是回忆中的故乡,所以就和现实产生了对比,就使回忆有了历史深度。这种回忆,是通过一以贯之的叙述者“我”来呈现的。“我”曾经在故乡生活,后来离开了故乡,因为各种机缘,又重返故乡,重遇和重提故乡的历史、人物和故事。
这种回忆,使得现实的真实性不再具有确定性。例如,在《火把与口哨》中写道,“这是1966年8月份的事,那时候的事,不能以常理论之,如今回想,如同噩梦,但噩梦中似乎也有浪漫与狂欢的成分,甚至还有艺术,这是否是少年的错觉,还真不好说”。另外,在时间的今昔对比中,消解了政治性。昔日的地主孙敬贤最后的婚礼,旁观的人“其实没人去关心这件事的政治意味,大家只是感到很热闹,很荒诞,很好玩”。乡土本身的生活逻辑过于强大,在历史的时间发展中被彰显出来。
时间物语术
时间和物候联系,和大地联系,呈现出乡土社会独特的记事和记时方式。时间并不单纯是钟表时间,也和大自然有着密切联系。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是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的变化规律而形成的,是农耕社会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时间。
在《晚熟的人》中,莫言就将时间和物候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时间物候似的叙事手法。例如,《左镰》中写道“每年夏天,槐花开的时候,章丘县的铁匠老韩就会带着他的两个徒弟出现我们村里,他们在村头那棵大槐树下卸下车子,支起摊子,垒起炉子,叮叮当当地干起来”。回忆的具体时间是和槐花开这一物候相联系的,也因此是明晰的、具体的、可见的,是被空间化了的。
再如,“我经常回忆起武功与村里最有力气的王魁打架的那个夏天。那天中午,我与母亲坐在我们院子里那棵杏树下挑拣麦秸草里夹带着的麦穗”,这样的时间物语术让整个回忆有了乡土性的审美。在现代性不可逆转的变迁中,有一种怀旧意识,从而在一个日益广阔和漂泊的世界中,建构起一个在回忆中具有完整性的主体认同。在《晚熟的人》中,《地主的眼神》开篇就提到“去年麦收时,我在老家,看到了老地主孙敬贤的葬礼。现在的麦收,与我记忆中的麦收,已经大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在钟声的催促下,鸡叫头遍时便匆匆起身”,接着“我”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记忆中的麦收是如何安静祥和。
风景的发现,永远基于主体对自我内在的发掘。日本著名思想家、文学评论家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就提到了风景的发现,风景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是一个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通过这个过程形成”。《晚熟的人》聚焦于回忆中的故乡风景,聚焦于返乡人“我”在现实和历史对比中建构出的乡土风景。这些被观照的风景“反作用于人类自身的情感、审美、心灵甚至主体结构,最终则涉及人类如何认知和感受自己的生活世界问题”。
时间预叙术
莫言在以往的小说中,非常善于运用时间预叙术。所谓时间预叙,是指提前将未来发生的事情叙述出来。小说中,经常出现“许多年以后”“后来”等时间表达方式。其目的,一是展示故事时间的长度,二是建构一种时空交错、故事交错的复杂叙事感。
在《晚熟的人》中,莫言将这种时间叙述术运用得更加炉火纯青。例如“许多年后,村子里的媒婆袁春花,要把寡居在家的欢子介绍给田奎”,读到这样的句子,读者就会产生好奇,继而期待之后的故事情节。再如,“许多年后,我认识了一个在国际比赛中屡获大奖的口哨王”“父亲后来告诉我,像武功这样的人,还真是不好对付,惹上了他,一辈子都纠缠不清”“后来我听杨结巴大叔说”等,都是时间预叙术的生动呈现。“后来”的时间,具备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从而对之前的故事进行了新的解释。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许是回忆起了蜡烛店的气味,而不是从三婶身上嗅到了这种气味”“写到这里,我真想就此结束,因为接下来的事情,我连回忆的勇气都没有,总是偶尔想到,便立刻回避,但如果我就此结束,显然又对不起听我唠叨了这么久的读者,那我就含悲忍泪讲下去吧”……《火把与口哨》中这段叙事,将“接下来的事情”的悲惨性预先告诉了读者。之所以要含悲忍泪地讲,是为了突出三婶在知道女儿被冤枉之后,去狼窝为女儿复仇,最后死去的故事。故事结尾,狼窝已成了旅游点。村里人希望在三婶的墓地建一个护子娘娘庙。进京找“我”出主意,“我”说:“你们不妨先建个纪念馆,纪念的时间长了,也就成了庙了,也就没人敢拆了。”乡村发展和乡土人的命运、性格,有着自身的逻辑。在此,叙述者“我”用时间预叙术将这种逻辑呈现了出来。
时间乡愁术
在《晚熟的人》中,作者频繁地、有意地使用各种时间法术,是为了表现一种浓郁的乡愁。这种乡愁,由故乡的人和历史组成,由一个个具体的物候组成,有时甚至由葱、馒头、炕等一些事物组成,例如“我抓起一段葱,蘸上黄酱,咣当咬了一口,这一下唤醒了我的胃,唤醒了我的豪气,唤醒了我的乡愁”“那家乡土地上生长出的小麦磨粉后蒸出来的大馒头,总是能引发我的乡愁”“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炕其实很小”等。
1934年,32岁的沈从文因母亲病危而从北平返回湘西,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写道:“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乡愁是重要一维。在《晚熟的人》中,莫言一改以往的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手法,而是以极度写实的笔触书写了故乡。这个故乡不再是单纯的乌托邦幻境,也不只是国民性象征的渊薮,而是一个既有历史纵深感,又在现实巨变中无比真实和复杂的故乡。这两个故乡,在“我”的各种时间叙事中得以同时呈现,耐人寻味。
(作者史静系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范楷系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