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吕澎
对于一般读者,专业的美术史著作多少有些让人望而生畏。除了专业壁垒之外,德国的形而上思辨传统构成了欧洲美术史的基础,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语世界才开始渐渐有了美术史的专门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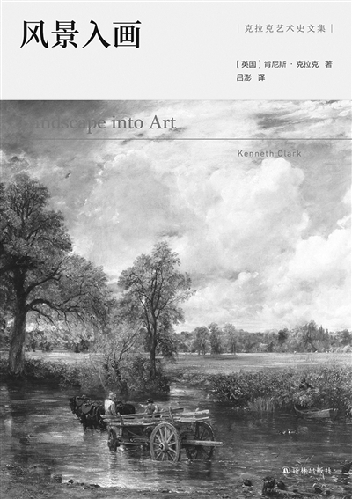
1
在英语世界扩大并普及美术史知识的进程中,英国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从二战开始,正是他使得英语世界的观众和读者获得了美术史知识,尤其是他所主持的大型纪录片《文明》,通过美术的历史向欧洲观众介绍了人类文明的历史。
《风景入画》(Landscape into Art)是克拉克的重要著作之一。从1946年到1948年,克拉克在牛津大学担任斯莱德教授,他的讲座延续了约翰·罗斯金的传统与使命:“让我们英国的青年人多少关心一点艺术。”斯莱德教授的职位使克拉克的讲座成为他后来很多艺术史文章的基础。而他在第一年首开的讲座是关于风景画的历史,讲座之后他将其编辑完成了他最好的著作之一,即这本《风景入画》。
与之前的美术史专著不同,克拉克并没有通过严格的流派或编年体例来组织风景绘画的历史叙述,他采取了将艺术风格与时代关系的方式来梳理欧洲风景画的发展。他尽可能省去了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的罗列,而将艺术风格问题作为介绍重点。所以,他的体例是根据主题来安排的:即“事实风景”“幻象风景”“理想风景”“自然景象”“北方之光”和“回到秩序”,这种体例很容易把读者引入作者讲述的世界中,直接进入风格、承继以及问题的分析与思考中。
正如《伯灵顿》杂志上的文章称,克拉克属于“从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到罗杰·弗莱这类艺术史上杰出的分析和诠释型评论家。他们的传统不同于德国人形而上的方法、意大利人的修辞风格、法国人流行的讽刺咒语、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学研究或时髦的图像学家的寓言。他们的方法属于经验主义……由对实际作品的热爱所激发”。实际上,克拉克非常容易让听众或者读者接受,因为他们一开始也是从对艺术图像本身的感受出发:经验引导着观众对画面的领悟,而这正好是克拉克的讲座和写作的目的——尽可能让大众对艺术有一个轻松的理解。
我们可以将《风景入画》看成是一部介绍欧洲风景画产生、发展以及丰富变化的历史,从凡·艾克到塞尚,作者展示了“在古典传统和理论家的一致反对中,风景画如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即人们长期视而不见的自然风景究竟是如何转变为绘画艺术的。克拉克不仅在艺术史,也在人文领域具备丰富的知识和教养,他在介绍风景艺术家的时候总是会跳出单纯的风格分析,而将同时期的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传统联系起来。例如,他在分析法国艺术家尼古拉斯·普桑的风景画的时候,与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联系起来,以便说明两者中具有同样的精神特质,在叙述中,不乏富于诗意的视野深度。
的确,读者能够从克拉克的叙述中,获得一些更为富于比较的理解,例如这位艺术史家告诉听众:在十四世纪,意大利人彼特拉克是西方“第一个为登山而登山的人,他登上山顶仅仅是为了饱览大自然的景色”。
2
读过瑞士人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读者能够看到,彼特拉克登山的感受已经被西方人完全神圣化和崇高化了。这样的精神境界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古代画家郭熙的看法:存在着一种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风景,这就是山水画。于是,我们在阅读克拉克的著作时,能够将东西方之间关于自然的看法进行有比较的了解,发现其差异与共鸣。
克拉克提及彼特拉克《书信集》第7卷第4书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是多么快乐地在山林间,在河流泉水间,在书籍和最伟大人物的才华间,孤独自由地呼吸着,我又怎样和大使徒一样地委身于目前的所在,设法忘却过去,闭目不看当前。
当彼特拉克登上高高的阿尔卑斯山眺望地中海和隆河后翻开了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第10章:
人们赞赏山岳的崇高,海水的汹涌,河流的浩荡,海岸的逶迤,星辰的运行,却把自身置于脑后……
实际上,当欧洲人对自然本身还处于小心翼翼的观看的时候,中国人已经画出了富于诗意的风景。肯尼斯·克拉克在讨论到西方风景画的起源时,提及中古时期欧洲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说作者还“想让我们分享他的恐怖”;欧洲在十三世纪前,基督教哲学僧侣观念还抑制着人们对森林和繁花的敏感性,以至“象征”或者符号化的图案成为早期欧洲人对自然物的谨小慎微的描述方式,一直持续到但丁在他的《神曲》里开始将自然的美同神性的美作比较,进而直至彼特拉克登上高高的阿尔卑斯山,欧洲人对自然风景的理解才有了彻底的转换。
对于熟悉中国山水画的读者来说,这些信息足让自己的内心感到抚慰并为自己的古人很早就对自然有了融入身心(所谓“天人合一”)的理解而感到骄傲。
3
当然,《风景入画》的主要目的是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了解欧洲风景画的历史,了解即便是对自然的描绘,也会受到神秘主义、宗教观念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并构成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流派。在艺术史专业领域,专家们总是尽量避免文学地描述艺术作品,然而,克拉克并不忌讳这一点。克拉克熟悉当时专业领域的各种研究方法,尤其是流行的图像学,但是,他试图在各种方法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对于克拉克来说,重要的是艺术,而不是概念与方法。
面对19世纪后期,尤其是进入20世纪的艺术时,艺术史家遭遇严峻挑战,风景画作为一种题材,在未来究竟是否能够得到发展?与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坚韧的文化立场不同,克拉克带着一种“对近代历史深感沮丧的悲观主义者的微弱乐观”态度:“作为一个过时的个人主义者,我坚信这个世界的科学和官僚主义,原子弹和集中营统统不会完全毁灭人类精神;而人类精神总会成功地以一种可见的形式体现出来。”这是克拉克面对现代绘画的判断。
在目前国内西方艺术史的翻译介绍中,《风景入画》是第一部纯粹讨论欧洲风景画艺术的著作,比起那些同时综合介绍不同艺术形式的历史著作来说,读者可以更为全面、不受干扰地了解西方艺术门类的一个分支,并在一种流畅而优美的文字叙述中获得艺术知识。的确,这是一本富于教养的艺术书,我们可以在作者克拉克去世时世界的反应看到“教养”在克拉克一生中的光彩。有人评论:“很少有艺术历史学家或者学者能够期待他们的死能像克拉克那样吸引国际媒体的报道。”仅在欧洲,从苏黎世到马德里、阿姆斯特丹、罗马和巴黎,很多报纸都报道这一事件。哲学家约翰·罗素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赞克拉克是英国文化生活中的杰出人物,也是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天赋的艺术史学家。在克拉克的追悼会上,耶胡迪·梅纽因演奏了巴赫d小调组曲中的恰空舞曲;他的朋友约翰·波普·轩尼诗发表演说,称克拉克“是一个用艺术家对作品意图和语境的理解来观看艺术作品的人”。(吕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