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江飞
读《燕食记》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被一种难以言说的整体气氛所包围,看完之后,依然久久地沉浸其中。这种体验是久违的,也是美妙的。由此我想到,在今天,一部优秀的小说,恐怕应该是一部有气氛的小说,应当具有本雅明所谓的“灵气”或“光晕”,能够让读者像置身于音乐、建筑甚至游戏之中那样,获得一种沉浸式的审美体验。随后我又看了刚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飞发》等中篇小说,再一次验证了我的感受,那就是,葛亮越来越善于营造某种氛围,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气氛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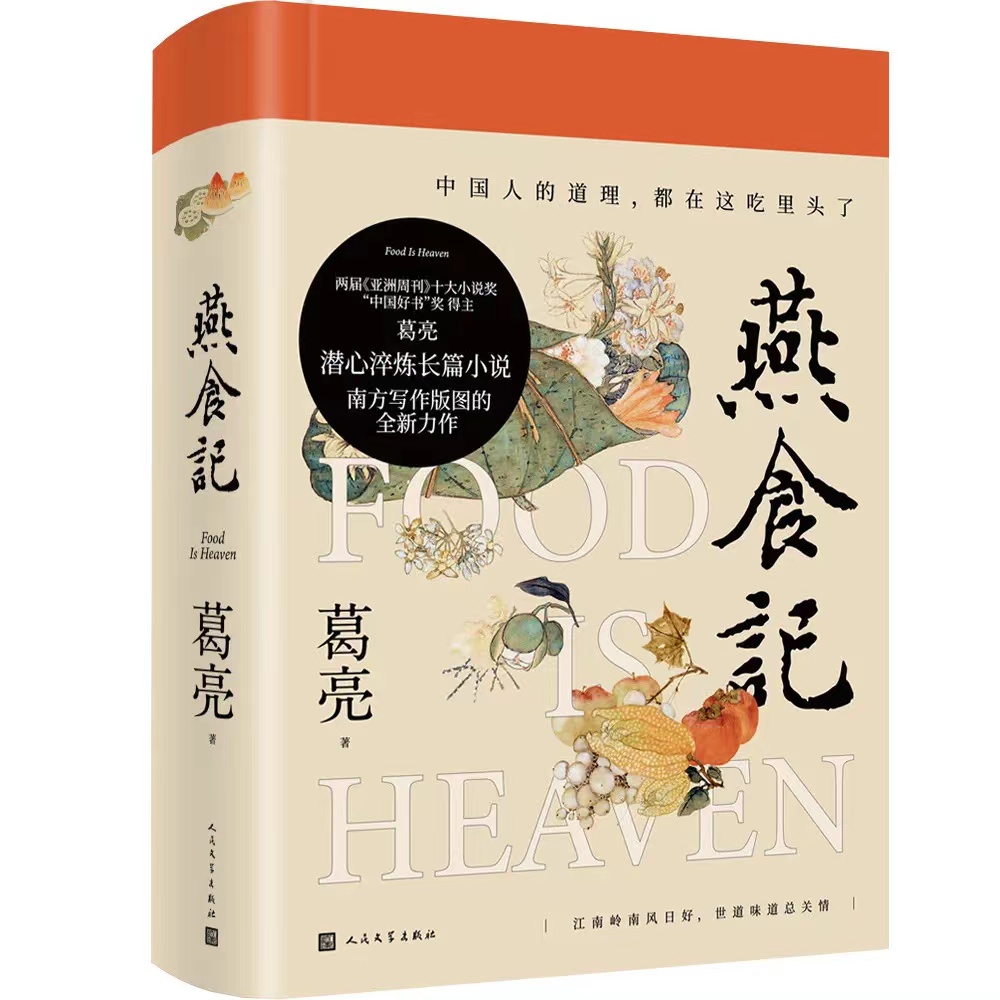
“气氛”(atmosphere)这个概念很常见,生活中往往会以愉悦的、庄重的、热烈的、紧张的等等来形容;但它又很陌生,无形、模糊,让人难以琢磨。德国哲学家、美学家格诺特·波默将“气氛”上升为美学概念和新美学认知的核心对象。作为新美学核心概念的“气氛”,是要摆脱主客体二元论,还原审美现象的开放性、模糊性,介于主客体之间的居间状态。它是一种“物的迷狂”,突破事物的物理界限和规定性,突出它们共同的时空当下的在场性;另一方面,也突破了意识的主观性,营造出一种气氛。园林设计、舞台美术、商品设计以及权力政治等,都是气氛制造者。在我看来,气质儒雅的葛亮也深谙气氛制造的奥秘,由“吃”入世,创造了一个雅俗共赏、食色一体、物我不分的艺术空间,高度浓缩了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美学,氤氲着中国文化的人生本色和民间伦理的情深意重。
很显然,《燕食记》是一部文火慢煮、“文气”四溢的小说,充盈着高雅的文化气氛。如果说《北鸢》是关乎民国文化的想象,那么《燕食记》则是关乎近百年中国文化的想象,葛亮把传统文化精神弥散在整部小说的书写空间中,其基石自然是岭南饮食文化。正如书封上的英文所示,“Food Is Heaven”,意译为“民以食为天”。在我看来,与其说人民是把食物当作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东西,不如说是在美食之中品尝生活的酸甜苦辣,学会“中国人的道理”,体味文化传统对个体精神心理的滋养,在“物的迷狂”中把苦痛的人间变成幸福的“天堂”。在传统文化里浸淫已久的葛亮,所擅长的正是“格物”,将“物”作为文化传统的代言者,托物言志,借物抒情,书写“物”的意义。比如他很喜欢诗人辛波斯卡的《博物馆》中的一句,“金属,陶器,鸟的羽毛,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他被这句话触动,而写了金属发剪、陶制瓦猫和古籍修复师除渍的羽毛,将之作为《飞发》《瓦猫》《书匠》三则小说中最重要的物象。因此,在《燕食记》中,粤菜也好,上海本帮菜也好,“熔金煮玉”也好,红烧肉也好,食物已不再是“物”,它突破了其物理界限和规定性,而成为意义的言说,成为“人”的不在场的在场,成为情感的寄托、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表征。小说首尾,师徒二人共同研制的鸳鸯月饼,一半莲蓉黑芝麻,一半奶黄流心,中间是一片薄薄的豆腐片,分隔阴阳,让二者各安其是,相得益彰,这无疑是周易文化的转化;韩世江凭阿响做的缺了一味的月饼,就断定叶七阴魂不散,而叶七的一封无字信又让阿响领悟到所缺的那一味是“盐”,咸与甜相克相生,这无疑是道家文化的现身。“三餐惹味处,半部岭南史”,葛亮所要表达的,不是时间战胜了美食,也不是美食战胜了时间,而是食物与历史、美食与厨师、饮食与文化相互成全,生生不息。
同时,《燕食记》又是一部非常“俗”气的小说,通篇弥漫着世俗的烟火气氛,其中最动人的莫过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儿女情长、历久弥新的民间伦理道德,贯穿始终的是中国人的“吃饭哲学”和处世哲学。从“多男”茶楼的啁啾声一片,同钦楼“大按”部马不停蹄造月饼的热闹,到太史第后厨的众声喧哗,再到湾仔或观塘“十八行”的人来人往,从商贾政客、革命志士、钟鼎之族、行会巨头等传奇人物到市井民生,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的沧桑变迁,都成为饮食男女悲欢离合的背景与氛围。荣慧生与叶凤池的相依为命,陈五举与戴凤行的相濡以沫,成为乱世中的暖色;而月傅与陈赫明私定终身却生离死别,荣贻生与司徒云重心心相印却爱而不得,五举与露露患难与共却不得不戛然而止,则坦陈出人间情爱的无奈与哀伤。荣贻生与陈五举的师徒情深,既体现在五举信守承诺、知恩图报,离开同钦楼后终身不用师傅传授的技艺,数十年逢年过节等候在师傅门口,也体现在师傅许多年后现身饮食大赛决赛,有心成全五举,让他赢得结实堂皇。时移世易,却自有一套“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伦理和道德准则绵延不绝,化解恩怨情仇、守护做人底线。正如陈思和先生在《北鸢》序言中所言,“中国传统做人的道德底线,说起来也是惊天地泣鬼神,在旧传统向新时代过渡期间维系着文化的传承”。文化的核心是人,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文化的传承归根结底要靠伦理道德维系和传承,这在消费时代和娱乐时代显得尤为重要。“江南岭南风日好,世道味道总关情。”《燕食记》告诉我们:这世界终究是以“情”为本体的世界,而人在世界之中,不过是像打莲蓉那样用心,耐心,慢慢“熬”,熬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熬到物我不分,主客为一,这便是人生的过程,正如葛亮所说,“所有事物的进程,自有其规律,类似草木枯荣。无声无息,其来有自。”
总之,葛亮别具匠心地将“文气”与“俗气”融为一炉,气氛营造得浓淡相宜,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加上古色古香的标题,雅洁精炼的白话夹杂着生动活泼的粤语方言,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交织互动,虚实相生的叙事,恰到好处的史料引用与考证化用,更重要的是,不光从“匠”的角度,而且从“人”本身的角度去体贴和理解“匠人”(厨师),为读者烹饪了这道色香味俱全的大菜。
(作者江飞系安庆师范大学美学与文艺评论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