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顾赵秋慧
“他在岛上是一个崇拜沉默的人;犹如一扇巨大的耳朵思索着这份沉默;每天都有密探前来报告,他宁愿自己的臣民去吟唱,而不是去说话。”
这段是英国作家罗伯特·史蒂文森在太平洋旅行时写下的。史蒂文森所说的“崇拜沉默的人”指的是阿佩玛玛岛的国王泰比诺克,一个独裁的暴君,通过武装恐吓牢牢控制着他的王国,除了特殊优待,决不允许异域人进入,锻造出一个封闭的岛屿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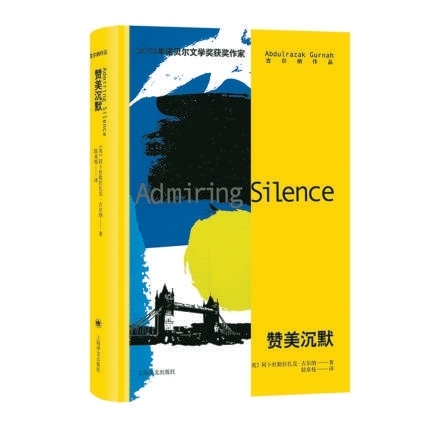
《赞美沉默》 【英】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将此引作《赞美沉默》第一部分的题词,隐喻了小说里桑给巴尔岛同构性的沉默。
一、以“沉默”为“沉默”言说
王小波曾说,沉默者的话语是强征来的税金,话语权占据了阳的一极,沉默者便被贬入阴。古尔纳、拉什迪等移民作家大约同样属于厌恶话语从而保持沉默的一类,古尔纳称这一类人为“赞美沉默的人”。《赞美沉默》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桑给巴尔在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独立仅一年,又在1964年遭遇了革命巨变,监禁、处决、驱逐随之而来,侮辱与压迫无休无止。古尔纳当时仅16岁,三年后他逃往英国,在那里重新开始生活。直到1984年,他才有机会重回桑给巴尔,见到临终前的父亲。《赞美沉默》的叙事者“我”所遭遇的正是来源于古尔纳自己的这段经历,“我”一面沉默,一面作出沉默者的言说——不止被话语权强征税金,并且充满了自欺欺人的幻想。
或许,这场时隔近二十年重返故乡的见闻与父亲的离世,对古尔纳产生了过去与现实交汇却无法相融的冲击。随后他在1987年写下处女作《离别的记忆》,开启了他的小说创作之路。《天堂》之后,他在1996年创作了《赞美沉默》,进一步思考那些从少年时期起就萦绕在心头的梦魇究竟是为何,以及怎样发生的。与此同时,残酷时代的逐渐远去,也让他不安地看到胜利者——话语权的持有者,正在别有用心地构建乃至重组一种简化的历史。他试图拾起那些被抹掉的记忆,以“沉默”为“沉默”言说。
二、“我”来自印度洋
小说伊始,在英国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我”,受困于心脏的痛苦而去看医生。医生对“我”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场种族论断:“非裔加勒比人心脏爱出问题。……他们容易患高血压、镰状细胞贫血、痴呆、登革热、昏睡病、糖尿病、健忘症、黄疸、多痰、忧郁和癔症。”
这仅是“我”二十年来生活境况的一个切片,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殖民主义残留下来的种族偏见在英国社会已如此顽固。“我”明白医生所说的“非裔加勒比人”,不过是“黑人、黑奴、黑佬”的代指,这类词语在医生的潜意识里投射出一个关于非洲的刻板想象,“饥荒、暴政、疾病、无尽欲望和历史受害者”。
于是“我”沉默着,在内心宣告“我是来自印度洋的少年”。这不是一个常见的关于故乡地缘认同的说法。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一片相邻的海洋。小说似乎并未强调一处明显的地理坐标,只在一处地点的注释里,我们方才辨认出“桑给巴尔”——东非漂浮在印度洋上的一群岛屿。
海洋缔造了广阔的岛屿并漫布于其间,航海及商业贸易往来联系了沿海地区。这正是桑给巴尔以及印度洋地区的地缘特征。当“我”重返故乡,每每试图掩饰从曾经的殖民国(英国)归来的“逃离者”身份、取得当地人的认同时,“我”使用的是斯瓦西里语。斯瓦西里地区所指代的东非沿海地带,即非洲大陆与印度洋的交界之地,在这里,东非曾与中东、阿拉伯、欧洲、亚洲等地区碰撞、融合,形成属于印度洋的斯瓦西里文化。对这一地区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共同享有这片印度洋以及海洋文明。这是小说的叙事者“我”,也是古尔纳自己的文化认同。
作为古尔纳书写的重要主题之一,移民是在故土与新大陆之间流动的群体。印度洋以及海上航线,使移动变得充满可能,而岛屿靠近大陆,与大陆的关系也同样微妙,那道分割岛屿的海峡,为岛屿既带来疏离的安全,又延续着脐带似的依赖。古尔纳曾在访谈中说到“海岛心态”,即“害怕出海但也随时准备出海——而非定居陆地、建造大城市的心态”。小说的叙事者,来自于印度洋的“我”,怀着这种“海岛心态”,呼唤在殖民主义下分崩离析的“我们”,寻找失落的“混杂性”。
三、漂浮者的“沉默”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细腻而忧郁地呈现出一个岛屿漂浮者的沉默,“我”看到过去与现在之间横亘着无法填补的鸿沟,恐惧于过去与现在互不相容的冲突。身处英国的当下,“我”对恋人爱玛隐瞒非洲的真实记忆,重构了非洲的往事;而面对非洲的亲人——母亲、继父、同母异父的弟弟阿克巴,二十年来“我”从不提及英国的真实生活,比如与爱玛同居,还拥有一个17岁的孩子……
回到沉默的最初时刻,“我”在英国租住在狭窄的一居室,没有地方放衣服,天冷无法开窗意味着要么忍受油烟,要么放弃开灶做饭;缺钱,又受限于学生签证没法工作,以至于最终应聘了洗盘工。古尔纳没有直接叙述“我”作为外国学生在英国遭受了怎样的轻蔑和歧视,而是讲述“我”遇到爱玛,与作为英国人的爱玛建立关系以后“我”身上的变化。
爱玛不仅仅意味着爱玛,还意味着英国对“我”的接纳。然而,爱玛认可赞许“我”,何尝不是奥赛罗式的呢?“我”的异族身份,在爱玛看来具有英雄气概,“首先因为我是历史压迫的受害者,这让我自然而然就博得了同情。”“我”知道爱玛想成为反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爱玛的父亲威洛比先生喜欢咀嚼英国给殖民地带来的光明,“我”的非裔身份和面具正好满足了这个英国家庭的需要。
在历史的阻隔中,存在着太多被言说构建出来的“事件”,由此人的观念、认识与想象也被言说者构建。正如古尔纳在2005年接受访谈时所说,主宰话语权的西方文化“向内看”,它们自己解释自己,相反,历史上殖民地在遭遇西方时,只得向西方解释自己,解释自己与西方的关系。“我”所遭遇的在他处的生活就是如此。“我”需要不停地向他者“解释”自我的移民处境,在移民身份的重复言说中,又怎能真正建立一个新的家园?事实上,“我”也并没有完全放弃言说的努力,但却在与爱玛之间争论中宣告失败,来自殖民地的移民只好接受爱玛代表的殖民国家带给的“个人主义、电冰箱和神圣的婚姻”(即使我们并没有结婚)。也许正是这些被压抑的反抗逐渐积攒,郁结于心,使得“我”患上的心脏疾病显得像是一种沉默的隐喻。
四、当“我们”不再是“我们”
时隔二十年,“我”重返非洲,迎面遭遇了后殖民时代的真实:污水管不通、马桶堵塞、下水道淤塞、屋顶漏雨、水电短缺……古尔纳用冷峻的笔调讽刺了东非在后殖民时代腐败无能的权力机关。
“我们”,是《赞美沉默》里出现频次不低的一个词语。古尔纳选择以实验性的叙述(第一人称的双重叙事策略),揭示了作家个人对“我们”——此类“虚拟的能指”“先验的能指”——所持有的抗拒。在小说里,他借助叙事者的回溯视角,痛切说出了对于“我们”的认识:“事实上,我们已不再是我们,我们呆在各自的院子里,封闭在历史的贫民窟中,自我宽恕并且满心都是偏狭、种族主义和怨恨。……我们开始考虑今后的自己,我们说服自己认为遭受虐待的对象并未留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或者他们已经原谅了自己并且现在乐意接受一种团结统一和民族主义的论调。”
如果稍微了解一下桑给巴尔的独立史,可以对这段话有更深的理解。桑给巴尔的本土人,历史上并不存在人种的划分,他们的情感认同归属伊斯兰文化。然而到20世纪初,英国殖民者以统治话语对殖民地进行种族划分,这种共同认同便无可挽回地被打碎了。当桑给巴尔开始走上摆脱殖民、争取独立的道路后,英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人种身份,又在桑给巴尔内部党政争斗中被强化为政治身份,导致桑给巴尔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与暴力。
“我们”的主体性被殖民历史、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幽灵入侵,又被种族主义瓦解。“我们”的碎片,禁锢在权力营造的种族意识里,蜷缩在虚伪的混杂性下,哀哀地沉默。古尔纳将这种被压抑的沉默,转化为小说叙事者的独白,以沉默者的潜在话语对抗权力者的殖民话语,试图找到那曾经诞生过斯瓦西里融合文化的真正的混杂性,使“我们”重获主体性,重拾自由。
五、漂浮者的找寻与出路
不同于上一代非洲作家(如恩古吉)把非洲视为家园或根,古尔纳让叙事者在他乡重构过去的记忆,又在重返亲历的现场把它们一一打碎。在他笔下,非洲绝不是“家”。而在小说的结尾,古尔纳又进一步剥离掉“我”曾以为是“新家园”的情感联系——恋人、孩子依次离开,亦不把欧洲视为出路。
古尔纳在小说中提供了一个直面“粪便”式的结尾。“堵塞的马桶”,一直在“我”重返故土的经历中反复出现,成为故土在后殖民时代的现实象征。也许同样身为逃亡者,古尔纳与昆德拉都看到了一种两极化的“媚俗”以及击穿“媚俗”的“粪便”。古尔纳从后殖民时代下的印度洋视角出发,思考漂浮者的希望与出路,试图找回那种牵连却不依附于大陆(无论是欧洲或是非洲)的海岛心态:不依附于任何中心,穿越重重边界,抵达混杂。这恰与小说文本的形态一致,他不作抒情,不吟乡愁,他让叙事者沉默的声音随着意识不断游走,建构出一个漂浮者自我找寻、辩护又与话语抗争的潜层语流。当“我”的记忆正式遭遇母亲的记忆,沉默与沉默在言说中交融,“我”得以重新拾起那个印度洋少年的自己。小说最后,“我”准备学习水暖课程以解决故乡马桶堵塞的问题,但却是“以外籍人员的身份”——漂浮者的出路所在——摆脱被构建的话语,却又以漂浮者的身份言说。(顾赵秋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