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陈 星
《英国鸟类史》是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底推出的新译著,属于该出版社聚焦环境与生态问题讨论的“同一颗星球”丛书系列。原著由英国脊椎动物学家德里克·亚尔登(已故)和动物考古学家翁贝托·阿尔巴雷拉合作完成,中译本的译者是古鸟类研究学者周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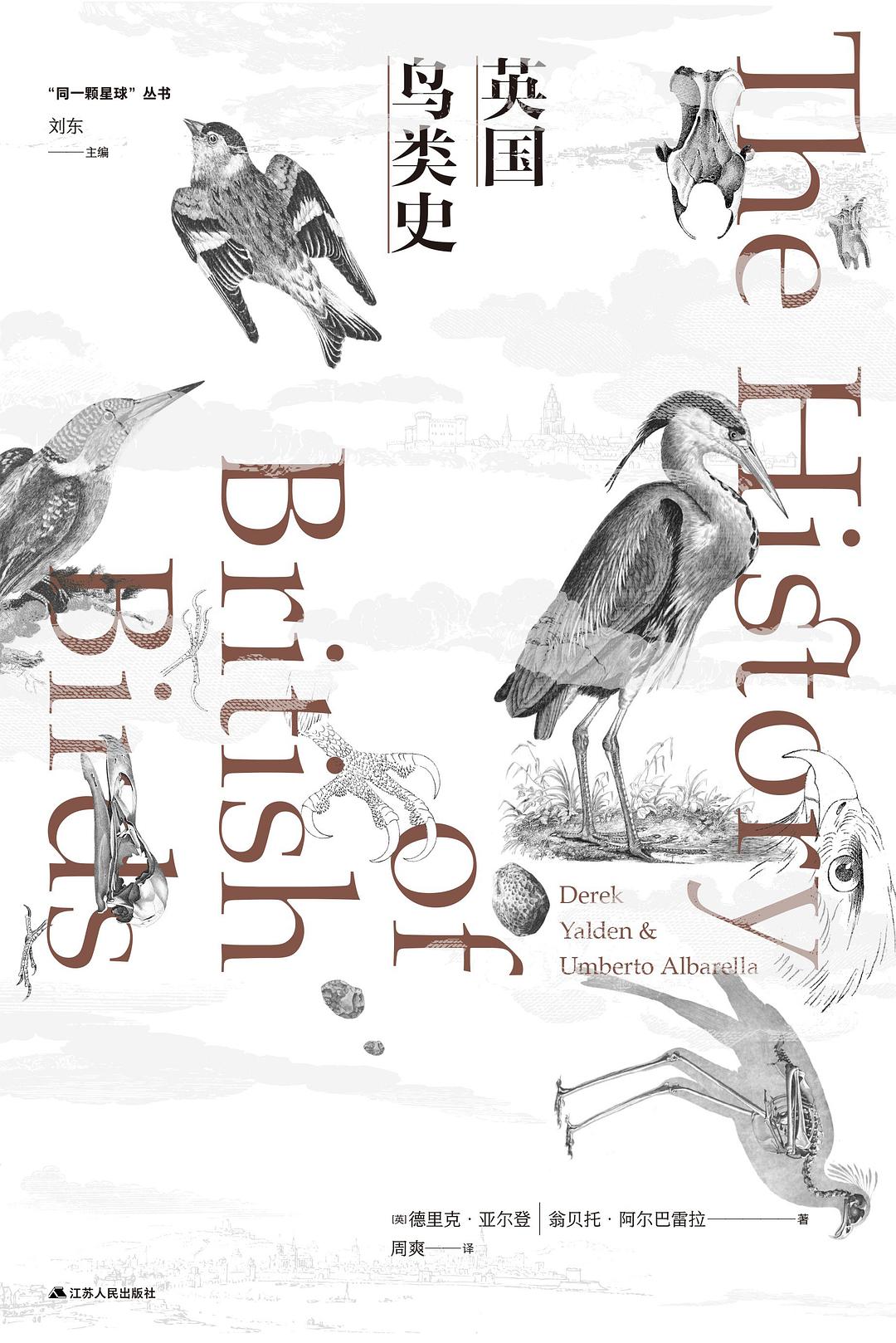
《英国鸟类史》书封
《英国鸟类史》向读者们介绍了中生代至今各时期不列颠群岛上鸟类种群的情况和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不同于我们可能更为熟悉的以情节性(起始——过程——结尾)为特征的叙事式历史书写,本书之“史”记叙的是不同时期不列颠鸟类种群及其生活环境面貌的考古实证与数据,并依据该数据和实证对具体鸟种的生存情况以及相关人类活动轨迹与习俗做出了一些谨慎的推测。全书的第一章简明扼要地解析了鸟类骨骼的特征,以及鉴定中可能出现的困难与解决方法。这一章是全书的引子和基础,指出有历史记录前的鸟类信息有可能通过其骨骼化石鉴定获得,这使得后续论述,特别是关于英国及欧洲大陆鸟类早期历史的论述得以展开。自第二章起,书中的史学记录大致按照历史时间排序,但在此大框架下,作者考察了某些鸟类栖息地(旷野、农田和沼泽)变化,并回顾了一些特定鸟种(比如家鸽、大鸨、[已灭绝的]大海雀、松鸡等)在不列颠的栖息史。当然,对于鸟类种群历史的还原,作者并不仅依赖考古发掘和田野调查,还提供了大量鸟类的图像和文字史料:书中的第六、七两章集中列举了不列颠地名、古代仪式记录、早期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乔叟与莎士比亚著作)中出现的鸟类名录。全书包含大量考古记录数据、各时期鸟类分布图示、各种文献内鸟类名录以及其他各类相关数据图表,书后还附有英国各鸟种的历史记录和简短注释,以及详尽的引用文献列表。正如中文版序言中周忠和院士所言,全书堪称一个“小型的数据库”。
可以看出,《英国鸟类史》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普作品,堪称专业性极强的学术著作,预设读者应具有一定的考古学、鸟类学以及地球史知识储备。对于已经或者有志于从事鸟类学、古生物考古、自然环境史等研究的专业读者来说,本书提供的鸟类骨骼鉴定、标本年代确定、文献档案搜集与解读、等方面的“英国经验”,会是十分有益的指南与参考。
在其英文版问世后,国外鸟类学术期刊上刊登出的、由业内专家撰写的书评中大多表示它同样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但坦白地说,我作为一个未受过相关科学研究训练的业余鸟类爱好者,在阅读《英国鸟类史》时常有“隔行如隔山”之叹——书内术语、史实、名录信息密集,原始数据量巨大,并不那么好读。而如果说英国本土的普通读者就生活在书中探究的那片土地上,因而尚能找到阅读此书的意义,那么我们中的多数人,即生活在另一个国度的非专业读者,若是“啃”这本《英国鸟类史》,又能有何种收获呢?
仔细想来,应该至少有四。其一,是我们可以获得关于英国鸟类和人文的有趣知识(并大大丰富我们的鸟类知识储备),例如我们熟知的、如今只栖息在东亚地区的鸳鸯,在35万年前的不列颠群岛上可能也曾有分布;在英国古地名中出现最频繁的野生鸟类是鹤,不过这其中大概包含一些被误认了的苍鹭;泰晤士河上的疣鼻天鹅分“有标记”和“无标记”两种,无标记的属英国皇室,而有标记的(喙上的人工划痕)则分属英国酒商行会和染匠行会,等等。
其二,是通过阅读此书,读者可以一窥不同学科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的异同,并看到跨学科研究的可能与必要。《英国鸟类史》本身便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两位作者一位专事脊椎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研究,曾参与过针对埃塞俄比亚本土哺乳动物的调查和记录,并著有《英国哺乳动物史》;另一位则是动物考古学研究专家,是《牛津动物考古学手册》的编者之一。若是按照国内现阶段的学科划分方式,两人分属理、文两科,他们的共事是文理跨界合作的出色范例,二人的研究背景与专长结合能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用,这在本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文理研究的差异与融通,对于非鸟类学专业出身的读者来说,或许在书中第六、七章里能有更直观的感受。如上文所示,在这两章中,两位作者通过考察文化史料,获得关于相关时期英国本土与外来鸟种的分布情况。对“地名中的鸟类”的探索建立在对古英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学研究之上(美中不足是盖尔语和布立吞语地名未及充分探究),而对“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鸟类”的探索则有赖于英国文学文化研究。以莎士比亚作品中提及的鸟类为例,这一部分的文献资料来源,主要是19世纪末詹姆斯·哈汀的专著《莎士比亚鸟类志》和20世纪初皮埃尔·阿科巴斯的网站“莎士比亚鸟类志”中对于莎士比亚戏剧与诗歌中所提及鸟类的统计和鸟种的鉴定。对于亚尔登和阿尔巴雷拉而言,这些材料帮助解答的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有哪些本土和外来鸟种”这一自然科学问题;而在莎学和早期现代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同样的材料,则是一系列人文问题的探讨起点:在早期现代社会,鸟类及其他动物如何影响“人类”的定义?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中,默认观众读者具有怎样的动物认知?这样的认知与早期人文主义的关系如何?这样的认知与我们当下的“人类”与“动物”认知关系又如何?曾经和将来对我们的社会文化发展有何影响?当然,对于这些有趣问题的探索,《英国鸟类史》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原始资料。
或许应该一提的是,《英国鸟类史》一书的汉译,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不同学科间合作的必要。——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欲妄议此书的翻译质量:译本可读性极强,充分展示出译者过硬的专业知识,流畅的翻译文笔,既尊重了原文文风,又不违中文语言习惯。但也许是学术训练背景的原因,专业为古鸟类研究的译者在文学作品、人物、地名以及历史档案的译名处理上,有一些不妥之处(例如《李尔王》中的“柯尼什红嘴山鸦”,应是康沃尔[郡]——Cornish——红嘴山鸦;1566年的“《Grayne”保护法》”,应是《谷物粮食保护法》——“Grayne”是英语拼写未标准化时期“Grain”一词的异拼;乔叟的“《库克的故事》”应是《厨师的故事》,“《富兰克林的故事》”应是《平民地主的故事》,“《召唤师的故事》”则应是《差役的故事》等)。当然,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小瑕疵并不影响读者对于书本主要内容的理解。
文理研究的交融,不仅仅意味着更多优秀的学术理论性成果的产出,更意味着对于当下种种社会实践的有益指导——这也是读者读《英国鸟类史》或可得到的收获之三。这一点,《英国鸟类史》中译本所属的“同一颗星球”丛书的主编刘东教授在总序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这一系列书籍的出版,目的在于“推动新一轮的阅读,以增强国民,首先是知识群体的环境意识,唤醒他们对于自身行为的责任伦理,激活他们对于文明规则的从头反思。”而具体就《英国鸟类史》而言,书中对于进入文明社会后,某些鸟种在英国本土的兴衰和人类活动关系的探讨,以及对于英国进入20世纪后人们对鸟类和环境保护所作的努力、所获的成果、经历的挫折,以及行动的不足等等诸方面的介绍,对于生活在另一片土地上、同样面临着环境恶化与物种锐减的危机、誓以守护绿水青山为己任的我们,是重要的提醒和经验来源。而在笔者看来,这些提醒中尤为重要的一个,是我们不能陷入“先进的科技手段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迷思——“观念的改变”,以及人类因此愿意在惯常的生活方式上做出一些改变与让步,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如果说上面的这一提醒更多地针对作为群体的全人类,以及相关领域相关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那么《英国鸟类史》对于作为个体的读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是我这样自诩“爱鸟”之人——则还有更具体的提醒,即需不忘初心,毋以爱鸟之名行害鸟之事,此为读此书的收获之四。书中有这样一段:
许多……观鸟者(也许是鸟类学家)……的鸟类鉴定技术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所沉迷的事情更像是集邮。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对珍稀物种的热情可能会导致其被骚扰,甚至是死亡(据说曾经发生过观察研究稀有鸟类的人追逐田鸡[Sora Rail]时,导致其被践踏而死)。(p. 258)
这虽然是在描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英国,却同样适用于当下的中国:随着摄影器材的普及和城市间交通的便利,国内目前有一支庞大且在不断壮大的拍鸟(常自称“打鸟”)队伍。而在此群体中,部分个体对于所能拍摄到的鸟种、鸟类行为、甚至特殊构图同样有着“集邮式”的追求,并为此不惜打破鸟类生活规律甚至破坏其生存环境(例如为了“画面干净”而修剪掉鸟巢周围遮挡的枝叶、将雏鸟从巢中掏出、通过声诱食诱辅助拍摄等,这类活动看似无害,但国内外研究都证实对于鸟类正常的繁殖与生活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鸟类因此受惊弃巢、致伤致死的新闻并不少见。实际上,就在去年初,国内便有拍鸟者过分追逐鸟种致其死亡的案例——受害的鸟种恰就是与前面引文中提到的(黑脸)田鸡同科的花田鸡。

《气泵中的鸟:一场实验》
在阅读《英国鸟类史》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收藏在英国国家美术馆中的那幅大型油画《气泵中的鸟:一场实验》:画的正中央,一人手持一个巨大的玻璃气泵,气泵里是一只身体扭曲、奄奄一息(亦或是已死?)的玄风鹦鹉;围绕四周的人们,面对这幅景象,有的聚精会神,有的忧心忡忡,有的低头掩面,有的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毫不在意。这幅画展示的,是十八世纪中后期流行的“科学巡回秀”上对于十七世纪波义尔真空泵实验的重现。在我看来,这幅画中似乎浓缩了《英国鸟类史》中的若干关键词:鸟类、科学、艺术、人类、生死。鸟类是科学审视的对象、艺术描绘的主题、人类进步的牺牲品;面对它们时,我们中有的人冷静理智,有的共情喜爱,有的视而不见;但我们似乎都凌驾于它们之上,能够掌控它们的生死,但就像画面前景里、鹦鹉正下方大玻璃杯中的人类头骨所暗示的那样,我们与鸟类乃至所有地球野生生物休戚与共,并无不同。画上,在神色各异的人群中,手持气泵的科学家直视画外的我们,仿佛在问“对这一切你觉得该作何反应?”归根结底,《英国鸟类史》也在问我们这个问题——不过,不同于画家,作者们给出了他们的答案:现在“是成为鸟类学家的最好时机”。(陈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