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刘涛
乔叶长篇小说《宝水》采用第一人称“我”(女主人公“地青萍”)的视角,以其所见所闻,向读者生动呈现了予城市怀川县宝水村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的人和事。小说叙事如行云流水,人物形象生动立体,语言风趣幽默,具有颇为柔滑细腻的质感。这部小说标志作者在长篇小说艺术创作上所能达到的新高度。小说题材贴近当前现实生活,社会关注度高,叙事节奏把控恰如其分,张弛有度,这些都是它的亮点。作为整部小说的灵魂,最能拨动读者心弦的,则是其对当代中国人文化之根、精神之根、生命之根的寻找与肯定,在此意义上,这部小说可谓典型的“寻根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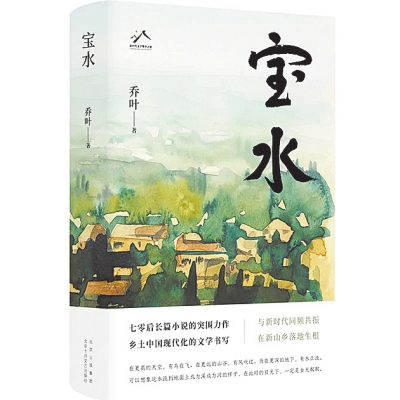
小说人物的命名和小说的故事情节蕴含鲜明的寻根意识。地青萍的“地”寓意“土地”“大地”。原承功小名“根儿”,“原根”即“根原”,有根本、源头、原始的意思。宝水村的“水”之所以被称为“宝”,乃是因为这“水”为生命之根。地青萍的宝水村之旅,本质是一次寻根之旅,她的最终落户宝水村,并与原承功结合,是根与地、地与水的融合,象征个体生命回归大地,找到生命之根,灵魂有了归宿。
小说中人物的结构关系同样包含鲜明的寻根意识。《宝水》中,小说人物结构关系可分两类,一类为同时共在关系,如“我”与宝水村村民的关系,其他村民之间的关系等等。小说中“我”(地青萍)与奶奶、九奶奶的关系,呈现为回忆视角下的历史对话关系。小说叙事开始于“我”的梦,梦的主体部分为“我”对奶奶王玉兰的回忆,之后,这种对奶奶的回忆,对童年往事的追忆,在小说叙事中不断呈现,回环往复。对于“我”来说,奶奶与福田村、老宅、童年生活是一体的。“我”对奶奶的一次次追忆,其实质是对我的故乡、故家、老宅、童年的打捞和寻找,是对自己生命、精神之根的寻找。“我”对奶奶的追忆,与“我”对奶奶的忏悔相伴而生。“我”的忏悔来自“我”对故乡的敌意、仇视和背弃。父亲的横死使“我”感觉到来自故乡的拖累,不自觉使用方言受到同学讥嘲则使“我”认识到故乡的落后和土气,这一切使“我”对故乡、对奶奶产生仇视和敌意。奶奶的死,“我”错过与奶奶的最后一面,使“我”产生顿悟,觉悟到个体生命与故乡、童年、过往的本质联系和难以割弃。背弃故乡即意味背弃自我。而无情斩断自我与故乡的关联,必然会导致个体身份的迷茫和生命意义的失落。小说中“我”与奶奶的纵向历史关系的叙事,显示出乔叶深沉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体现为自我对个体历史的反顾,对生命来路的寻找,对精神家园的回归。
小说还叙写了“我”与九奶奶之间的亲密交往。“我”与九奶奶之间的结构关系,同样是历时性而非共时性的,其意义指向“过去”而非“当下”。九奶奶名分上虽不是原家人,但其实是原承功的亲奶奶。接生婆九奶奶小名叫迎春,“我”的奶奶小名也叫迎春,两人不但名字完全一样,关系也非常亲密。小说中“我”第一次随原承功来到宝水,首先迎接他们的就是九奶奶。在九奶奶眼里,“我”就是原家媳妇。在“我”与九奶奶的深度交往和精神交流中,贯穿着“我”对宝水村历史和优秀传统的追溯,对原家人家族历史的寻找,同样显示出作者强烈的寻根意识。
小说的寻根意识还体现在大量方言土语的使用。语言尤其是方言土语,承载大量历史信息,一个民族的精神、情感和生活密码就隐含于其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在《宝水》这部小说里,乔叶变身为语言学家,具有高度敏锐的语言意识和卓越的语言发现、语言感知与语言运用能力。在她那里,语言不仅仅作为工具被使用,语言还作为叙事的艺术目的和对象,被塑造,被分析,被深描。小说主人公“我”和童年、故乡、过往的关系,同时体现为“我”与故乡方言的关系。“我”与“父亲”在家庭生活中对故乡方言的使用和痴迷,是其纯真的乡村情感的自然体现。大学时期“我”对故乡方言的断然拒斥,则显示出“我”对故乡和自我历史的自觉清理与拒斥。“我”来到宝水村,受村支书大英之托筹建村史馆,搜寻、收集村民家中的老物件,伴随这些老物件被发现的,还有大量生动形象、表现力超强的方言土语。如果说老物件是农民历史生活的物质遗存,是农民过去劳动生活的活化石,那么,活在人们口头上的方言土语,则是一个地方人民生活经验、内在情绪、精神生活的活化石,由此可窥测到不同地域人们不同的生活习俗、喜怒哀乐、性格心理。小说中,“我”的宝水村“历险”充满大量发现,既有风景的发现,又有美好人情风俗和过往老物件的发现,更有对方言土语的重新认知和发现。小说名为《宝水》,在整个小说叙事中宝水村叙事当然占有最大比重,而在宝水村叙事中,方言土语叙事则占有重要地位。为什么作者如此重视方言土语?这同样与作者的寻根意识有关。中国人乡土生活的所有秘密皆凝结沉淀在一地的方言土语中,方言土语不但是我们民族的语言之根,还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之根,欲望之根,情绪之根,我们生命个体的潜意识、隐意识,皆深深藏埋其中,等待着作为语言学家的作家去发掘,去表现。(刘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