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郑乃勇
《舍陂记》是一部独特的故乡传记。作者以故乡——舍陂村作为叙事空间,以散点透视的笔法,写出了立体化的故乡形象:一是围绕故乡的山川草木、蔬菜瓜果、自然风物等,写出了故乡的自然形态;二是在对故乡的衣食住行、世故人情、民俗歌谣、故事传说的讲述中,写出了故乡的文化形态;三是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为中心,写出了他们在生老病死循环中充满了痛苦、无奈、挣扎与坚韧的生命形态;四是将故乡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中,写出了故乡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形态。当然,这四种形态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融,彼此缠绕,从而完成了故乡形象的塑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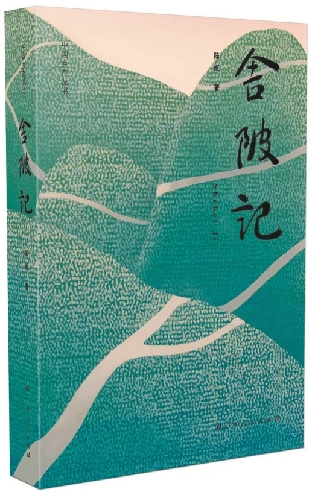
《舍陂记》 广西人民出版社 陈纸 著
《舍陂记》也是一部关于作者自我的传记。作者将自我植入对于故乡的叙述中,植入故乡一切有形和无形世界中,不仅构建了一个故乡形象,同时也构建了一个自我形象,这个自我既是故乡的叙述者,又在对故乡的叙述中呈现自身,故乡与自我互相型塑。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孤独绝望的农村少年怎样一步一步地成长,看到一个自卑厌学的农村少年怎样执着追求自己的梦想,看到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陈长庚”蜕变成具有文化气息的“陈纸”的艰难历程,可以说,《舍陂记》某种意义上也是作者的自叙传。
《舍陂记》的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感伤和忧郁情绪。细细地阅读和体会,我们会发现这种感伤和忧郁的情绪内涵极其复杂,其中,有游子“日暮乡关”的伤感,有“疼痛村庄”的悲悯,有生命消逝的忧伤,有青春不再的感怀,有时间无情的慨叹,还有精神还乡的渺茫,这些情愫流淌在字里行间。从更大的历史视野看,这种感伤和忧郁蕴含了作者对故乡由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全部复杂情感:一方面,“现代”就像一辆奔驰的列车,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另一方面,人们对传统又怀有真挚和强烈的依恋。
《舍陂记》的叙述视角是多重的。首先是儿童视角。儿童没有成年人的世故,也没有成年人成熟的主客体意识和鲜明的是非观,因此,儿童视角下,故乡是新鲜的、活泼的、单纯的、天真的,也是快乐的。其次是少年视角。少年虽然还没有完全成年,但他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对自我生存环境的感知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少年视角下,故乡也失去了那种单纯的快乐,他对故乡的情感体验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充满了抗拒、焦虑、忧伤、自卑、茫然,甚至痛苦。再次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视角。《舍陂记》中我们总能感受到有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具体地说,这个知识分子就是已经离开故乡多年,生存于现代都市的作者本人,他一方面对故乡怀有浓郁的乡愁,另一方面又有十分自觉的现代理性,这个知识分子时不时会跳出来,表达自己的理性思考。这三种视角在《舍陂记》流畅自由地转换,彼此穿梭,交融,从而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既有丰富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同时又充满理性思考的乡土世界。
阅读《舍陂记》,一个深刻的体验就是亲切。这种亲切感,一方面源于作为他的同乡、同学,我们有着十分相似的人生经历——他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他所经历的一切苦难和艰难,我都经历过,《舍陂记》中所叙述的一切人事和情感我都有深切的体会;另一方面,这种亲切感也与《舍陂记》的语言风格有关。《舍陂记》语言通俗质朴,亲切清新,他经常将地方语言融入规范现代汉语中,有我生活了几十年的浓郁的故乡特色和泥土气息。《舍陂记》有鲜明的记录性,没有什么绚烂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神秘的技巧,甚至叙述语言有时显得有些琐碎和唠叨,但这种琐碎和唠叨中有一种深切的情感,也与回忆性的情境相统一,故乡的点点滴滴,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正是在这种琐碎唠叨而又亲切的语言中召唤出来。
“舍陂村”只是中国大地上一个普通的乡村,除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与这片土地曾经血肉相连的人,估计很少有人过多关注这里发生的一切,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喜怒哀乐,它不过是时代缝隙中遗落的光影。然而,对这片光影的关心,某种意义上又是对整个中国的关心,这大概就是《舍陂记》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