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张晓东
作为世界文学的著名IP,我们对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似乎都不陌生,这个150年前的文学形象甚至非常具有当下性。一方面,她似乎被女性议题热点视为女性解放的形象,另一方面,在容错率极低的语境下,她又会被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人骂个体无完肤。总之,一个名媛的婚姻、爱情总是有吸引力的。所以今天我们依然在电影、音乐剧、芭蕾舞甚至花样滑冰中一次次重复这个“出轨”的故事,似乎连托尔斯泰也被这种“一定要爱情啊”的女性叙事惯性捕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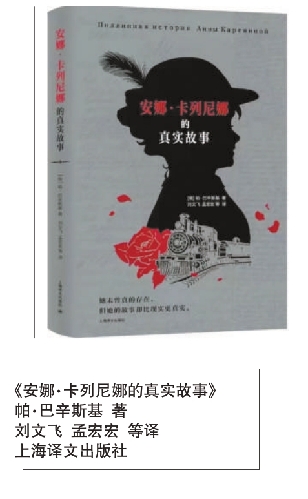
然而,绝非如此。甚至,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看,安娜·卡列尼娜都不是另一个包法利夫人(虽然托尔斯泰显然知道福楼拜的文学意义)。1870年代,是列夫·托尔斯泰遭遇更深的思想危机、继而试图去解决的年代,《安娜·卡列尼娜》是由此而来的一部艺术—思想杰作。在小说的双线结构中,康斯坦丁·列文的线索不仅使小说具备了历史—哲学的厚度和深度,也让小说散发出惊人的艺术魅力,就像托翁铁粉纳博科夫说的那样,这个结构让小说的“七个主要生命获得时间上的同一性”。这种共时性如果用电影来理解,就好比有极为复杂、多层次场面调度的景深的电影,就像电影大师雅克·塔蒂的《玩乐时间》那样(巧合的是,塔蒂的爷爷正是时任帝俄驻法国大使馆武官德米特里·塔蒂谢夫伯爵),然而达到这样景深的电影迄今还没有被拍出来。
即便只从安娜的线索来理解,“出轨”显然也包括了火车的、铁路的事故,它指向帝俄现代性进程中一种强大的、扭曲的、摧毁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语)。同样让安娜感到惊恐的不光是“爱情”不在,更是她厌恶并无法直视的那个扭曲、病态的自己,她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自然地、如其所是地行事,这是她的(也是卢梭影响下托尔斯泰贵族主人公的)无法承受之重。如此说来,难道我们认识了一个假的安娜?那倒不是,而是因为托翁的安娜有着强大的、暴风雪一样的精神力量,这使得她的形象超越了文本本身,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她。《安娜·卡列尼娜的真实故事》一书就提供了这种可能。
作者帕·巴辛斯基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学者,托尔斯泰研究专家,曾经是布克奖评委。不过,这本书倒并非是那种艰深的学术著作。巴辛斯基深知这本书有着无数的“普通”读者,他们的主要兴趣点都在美丽的女主人公身上——因此他采取了这样的写作策略: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安娜·卡列尼娜,也就是说,你们之前可能认识了一个假的安娜·卡列尼娜,那个“爱疯”的女人并不是她本尊。我这里有她的“一手大瓜”。
“真实故事”当然不是否认这个艺术形象,而是首先试图揭示出安娜的形象也是来自多个模特儿,最后“抟成一个”。同时这也意味着要理解这个形象还是得深入产生安娜的真实“土壤”。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几个安娜的“来源”:托尔斯泰庄园邻居的家庭女教师安娜·皮罗戈娃,她因为情变卧轨自杀,这为作家提供了一个主要的情节线索;普希金的长女玛丽亚·加尔通格,她那种异域的神秘高贵气质,个性的黑裙,悲剧的婚姻,都为安娜的形象塑造提供了参照。当然,这里还有文学形象之间的参照,巴辛斯基将安娜称为包法利夫人“同母异父的妹妹”(父亲是文学),普希金在《别尔金小说集》中未完成的作品《宾客聚集于XX别墅》也被认为提供了安娜形象的灵感来源。托尔斯泰其实并没有详细描述安娜的外表,他只需写出她旺盛的生命力,写出她对别人造成的“惊艳”效果即可,甚至也包括在安娜自己的眼中,“她看到了自己的眼睛在黑暗中的闪光”。难怪,世界各国有如此之多的影视剧版本《安娜·卡列尼娜》,但没有一个影视剧中的安娜形象能够获得读者大概率的共同认可。或许这也是巴辛斯基将导演和演员论《安娜·卡列尼娜》列入附录的原因。
巴辛斯基这本书试图告诉读者小说中的内容与现实生活中的“取材”问题,“小说的素材由种种事实的众多组合搭配,这些事实源于对周围生活的观察、作家的个人经验、作家专注研究熟人性格并深入其隐秘内心体验而产生的心理情境。这一切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出来。”作者的“考据”并不是学究行为,而是告诉我们这些艺术形象为什么是“活生生的”,因为这些素材都是“活生生的”。举个例子,小说第五部,列文的哥哥尼古拉·列文临终的那章描写,是世界文学中死亡书写罕有可比的,精准又震撼。司祭说垂死的列文:“他去了。”“但是,垂死者粘在一起的胡子突然微微动了动,寂静中响起一个发自胸腔深处清晰而明确的尖锐的声音:‘还没有……快了。’”实际上这个细节来自于托尔斯泰一家熟识的基谢廖夫死去的真实细节,而且他当时也处在不合法的、悲剧色彩的同居关系中。
应当指出的是,这些考据细节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例如关于小说有一个不容易想明白的问题,即安娜为什么没有离成婚,而且在弗龙斯基多次催促、卡列宁基本上已经应允的前提下安娜反而产生了延宕?“俄式离婚”这一节就提供了可靠的答案,不了解当时俄国的离婚法,是不可能读出其中深意的。实际上最需要安娜与卡列宁解除婚姻的是弗龙斯基,因为他盼望有个儿子(因为女儿是非婚期间所生,按照法律不可能姓弗龙斯基),但只有安娜和他有合法婚姻方可如此。而当时离婚是非常复杂的,由专门的机构,即教会宗教事务所负责。离婚必须提供充足的理由:1、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失踪)五年;2、夫妻一方无生育能力;3、夫妻一方出轨。显然安娜的离婚只能适应第三条,即安娜自己出轨。但是法律中还有一条规定,那就是出轨的一方无权再婚。那么实际上安娜办离婚的可能性只能是说服卡列宁谎称自己出轨。只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后续情节的进展。这场离婚变成了一种道德责任,对于贵族来说这是要命的,卡列宁最早提出离婚,实际上是要宣判安娜和弗龙斯基是一对“狗男女”,让他们永远不能有婚姻,随后他放弃了诉讼,这意味着他的某种道德崇高、宽宏大量,而这种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姿态让安娜更加厌恶他;如果之后他应安娜的要求离婚,即意味着他自己承担污名,这是一个更大的道德牺牲姿态,这是安娜无法去做的根本原因。而托尔斯泰写得如此深入,也与他的妹妹遭遇了类似的离婚诉讼有关。这也说明,文学研究不可能只是“内部”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中俄两国几乎是同步出版的,俄文首发式于2022年6月在莫斯科举办,实际上2022年3月中文翻译已经开启,并于7月完成。这也意味着中俄文明互鉴的“加速度”。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文艺》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