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头“鳄鱼”
——读莫言长篇话剧剧本《鳄鱼》
作者:江飞
“毫无疑问,贫富与欲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痛苦或者欢乐的根源”(莫言《悠着点,慢着点——在2010年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痛苦是人生的本质,而欲望是人的全部密码,用叔本华的话说就是,“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三十多年前,莫言就曾写下长篇小说《酒国》,描绘了荒诞又真实的人间欲望和人性沦陷,深刻揭露和分析了腐败的根源。这一次,转型为剧作家的莫言,经过十多年的构思,以四幕话剧剧本《鳄鱼》实现了对“欲望”和“反腐”主题的接续与创新,“不为英雄树碑立传,却为贪官写话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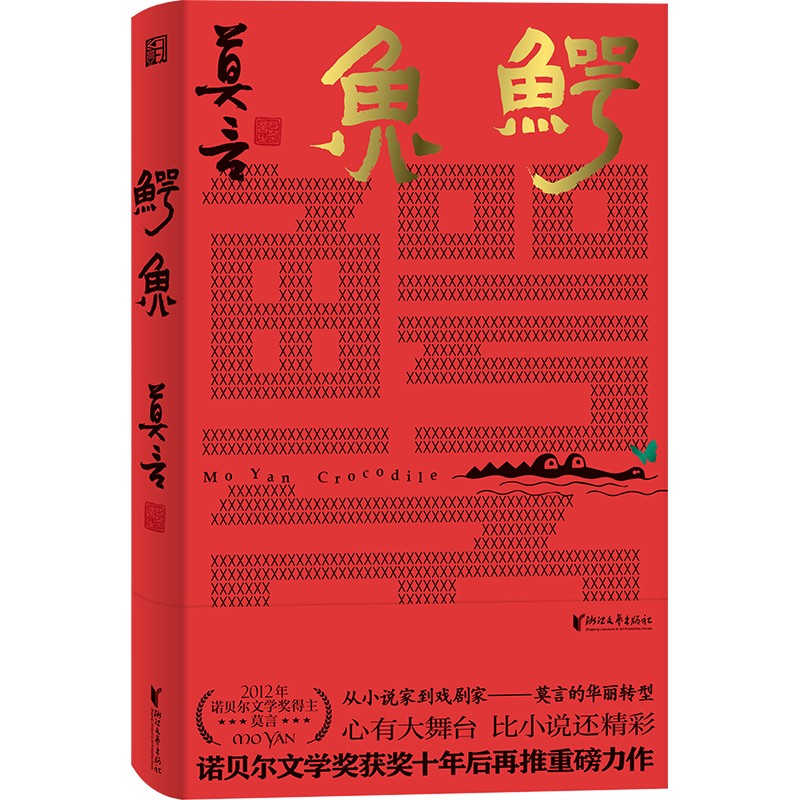
与其说这是一部“以逃亡贪官为主人公的话剧”,不如说这是一部以“欲望”或欲望的象征——“鳄鱼”为主角的寓言。在“后记”中,莫言就直接言明了这一主旨,“人的欲望就像鳄鱼一样,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和营养,便会快速生长。在本剧中,决定鳄鱼生长快慢的是养它的柜子,而决定贪官贪腐程度的是他掌握权力的大小与制度对权力的限制程度”。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是喂不饱的鳄鱼,如果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那么,像单无惮这样的贪官无疑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豢养鳄鱼最终葬于鳄鱼之腹”——这无疑是对所有贪官的警示教育。
在我看来,“反腐”其实也只是莫言使的一个障眼法,目的还是对贪官单无惮进行灵魂的揭示和反思,或者说以此为标本,在人性和个性上对官员共同贪腐现象进行深挖。很显然,莫言对当下某些小说、影视作品中塑造的那些概念化、扁平化的贪官形象是不满意的,而在《检察日报》多年工作的实践经验为其塑造单无惮这“一个能在舞台上站得住的典型人物”提供了条件。单无惮的典型性,正如会说话的鳄鱼最后对他所做的“庄严宣判”:“作恶多端但良心未泯。畏罪逃亡却热爱祖国。喜欢女人却终被女人抛弃。满怀壮志却一事无成”。人性的共性与个性统一于一身,悖谬与反讽也集合于一身,最终成就这一个“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与其说他是一个“罪该万死”的大恶人,不如说是一个因为放纵欲望而家破人亡的可怜人、失败者,用剧中老黑的话来说就是,他“不过是犯了一个仪表堂堂、手中有权的男人最容易犯的错误”。而之所以能够塑造这个典型形象,是因为莫言不是把贪官当成贪官来写,而是“当成人来写”,不是简单地批判,而是“了解地同情”,因此这个“人”的特殊构成是“五分英雄,二分流氓,二分情种,一分诗人”。我甚至觉得他不像是学中文的而更像是学哲学的哲人、智者,因为他时不时地就会像尼采那样妙语连珠,比如他说,“人民有心,人心所向;人民有眼,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有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人民有手,人民的铁拳砸碎旧世界;人民有耳朵,人民听到了你的召唤;人民有身体,把人民的冷暖挂在心上。人民什么都有,自然也有肛门。”把抽象的“人民”概念具象化,把人民的力量具身化,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戏谑中又蕴含深意。这是单无惮的表白,更是莫言自己的心声;这是对人物的个性和丰富性的尊重,更是对现实和艺术的尊重。
莫言巧妙地将一群贪官污吏、文痞艺丐、情妇赌徒置于美利坚合众国的一栋别墅里,为名份的瘦马,为金钱的慕飞和老黑,为虚名的牛布,为儿子的巧玲,如此等等。尽管身份各异,但每个人都是欲望的奴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头鳄鱼,可能是扬子鳄,也可能是奥里诺科鳄。单无惮逃出了祖国的怀抱,却无法逃出欲望的密室,罪恶的牢笼。莫言意在告诉人们:欲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可控的欲望催人奋进,超越理想,失控的欲望使人疯狂,堕落沉沦,并且必然导致“人人都是害人者,人人都是受害者”的互害型社会。“良心上过不去”的人毕竟是少数,仅仅依靠道德教化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要避免单无惮的悲剧,就必须“从制度设计上防止腐败,用法律来控制纵欲”,从而把心中的鳄鱼关在有限的心房里——《鳄鱼》的社会关切和人文关怀正在于此。
总而言之,“鳄鱼”不仅生长在每个人的心中,也盘踞在每个国家的心中。“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需要克制欲望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只有克制欲望才能实现。一个人的欲望失控,可能酿成凶杀;一个国家的欲望失控,你就会酿成战争。由此可见,国家克制自己的欲望,比每个人控制自己的欲望还要重要”(莫言《悠着点,慢着点》)。这句话的预见性不言而喻,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要控制自己的欲望,都要“悠着点,慢着点”,这或许正是《鳄鱼》想要表达的超越反腐、超越个人、超越国别的真正意图所在,是莫言的“世界情怀”所在。当然,莫言也十分清楚,文学也好,话剧也罢,并不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但也诚如其所言,“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话剧《鳄鱼》正是莫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一次努力,让我们也共同努力,继续与“心中的鳄鱼”搏斗吧……
(作者系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