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王辉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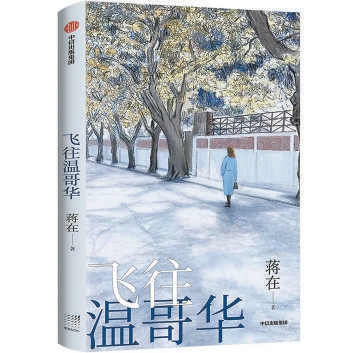
《飞往温哥华》 蒋在 中信出版集团
异域性写作,这是青年作家蒋在小说中的标识。它是如此的鲜明与强烈,仿佛成为了蒋在身上唯一的标签,以至于她不得不在《飞往温哥华》的后记中,发出告别的宣言:“飞往温哥华,看上去是开始,其实是一种结束。这个书名的恰切,如同一段时间的标识——它意味着某段异域性写作生涯的终结。”
其中缘由,是蒋在生命经验与视野悄然发生变化。她已不再是“中国人在温哥华”,而是“异乡人在北京”。日常生活中所积攒的经验,与其他生活在北京或大城市的作家相比,大抵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信息与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素材与经验同质化是作家不得不面对的尴尬。事实上,作品的卓越与否,并不取决于素材与经验,而是取决于作家的观察与认知:是如何观察生活的,又是如何对生活发出追问的?最为重要的是作家如何认识自我、如何梳理与叙述经验的?这一切,将会决定小说所能抵达的高度与深度。
事实上,当我阅读完《飞往温哥华》后,最触动我的并非“异域性”。同名小说的背景尽管发生在温哥华,但其内核却是我们无比熟悉的:一位殷切的母亲,对孩子寄予过高的希望。孩子在这希望中孤独前行,终于不堪重压,患上抑郁症。一个乖巧而努力的孩子,在异国他乡独自承受着经济的拮据、孤独的压力。家庭内部关系的离析,看起来处理得很好,犹如数学公式那么工整、优雅:夫妻和平离婚,对孩子的安排理性而周到。然而,最为感性的沟通却被这巨大的沉默给吞噬了。每个人都在报喜不报忧,都在“习惯了隐藏不好的那部分自己去承受”。孩子不告诉母亲自己的困难,妻子不告诉丈夫孩子的情况,丈夫亦忙碌着,开启了“被不在场的一生”。国人情感表达羞涩而含蓄,许多时候会将情感压抑在心底,尤其是负面的情绪。在情感表达方面,许多人大约都是“病人”,害怕自我展现,又厌恶他人表达。小说的结尾,孩子崩溃痛哭,让这个分离的家庭重新聚集在一起,似乎“有了新的开始”。然而,真实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因为“天车闪烁在大雪的夜里,一次又一次开向她并不知道的地方”。(王辉城)
压抑的情绪是宣泄了,家人似乎是和解了,然而生活并非瞬间,并非是个片段,而是漫长的、绵延的长河。我们观望他人的人生时,难免会生出许多豪情与壮志,似乎可以避免出现任何差池,但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人生往往却是茫然无措。因此,我们会有“再来一次”的愿望,似乎重启人生就会避免犯下任何过错。收入集子中的《再来一次》,便有着这样强烈的愿望。这是一段跨国恋,男女双方在恋爱的过程中,有甜蜜的回忆,也有相互折磨的痛苦。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方面的冲突,显得那么扎眼。小说的开头是“我们能否再试一次”,仿佛生活是场实验,两人相恋并非为了生活,而是为了复现某种浪漫。他们在西贡实验过(像极了《情人》,不是吗?),又试图在中国实验,试图在旅行中点燃爱情。然而,一场车祸却让实验终止了。恋人死亡了,“我”陷入了无限的悔恨中,幻想着“再来一次”。两人没有如愿以偿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上了那辆不该上的车。一定是。”生活自有逻辑,意外或许改变命运走向,但更为细微的、不愿承认的暗流早已波涛汹涌。意外只是催化剂。
蒋在所捕捉的情感与状态,跟异域性几乎关系不大,而是人类普遍、共通的情绪,是对广阔现实的精细描摹。《小茉莉》如是,《遗产》如是,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小说所发生的“都不是一定要发生在异国不可,小说着力描绘的那种巨大的失落感,显然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当代症候。”
回过头来去看蒋在的首部小说集《街区那头》,便会发现“异域性”曾是当仁不让的。在这部小说集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于国外,确切地说,发生在加拿大温哥华。这与蒋在的经历相关,她曾经在温哥华留学。因此,《街区那头》中的情绪与感受,几乎都是学生时代的:生活在同一个宿舍里因为身份不同而发生的龃龉,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种族歧视,等等。在多篇小说中,蒋在都写到参加教会的情节,这是局外之人尝试着融入当地社会中的努力。然而,这些举动更像是表面的仪式,小说中的人物试图以此获得他人的认可。更为深刻与巨大的鸿沟,潜藏在表层之下,且难以逾越。
最深刻与最彻底的“异域性”是《街区那头》一篇:主人公是黑白混血儿,名字叫卡拉(多么常见的外国名字啊)。母亲是非洲难民,父亲则生活在底层,做着上不得台面的灰色生意。卡拉有向上的雄心,亦有逃离的欲望。然而,在外面的世界溜达一圈后,卡拉灰头土脸地回到家中。母亲出轨的传言,让卡拉与父亲都相信,彼此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母亲的出轨对象据说是名银行家,这让卡拉燃起了寻找亲生父亲的欲望。卡拉确实也行动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此位银行家是位黑人女性。
若说真的让人感到“意外”,也不尽然。熟悉创意写作的读者,大概能预料到这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是标准的、工整的创意写作,但它与生命体验无关。如果遮蔽作者名字,我们会毫不犹豫认为是欧美作家的作品。如此熟稔地调动着身份与种族的筹码,如此娴熟地操控着情节——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时常怀疑这篇小说是蒋在的课堂作业。在《街区那头》这本书中,蒋在优秀的才华与叙述令我们赞叹,但更多时候,我们会感到她的迷茫与慌张——她不知道怎么在小说中处理自我,正如她在温哥华时的茫然。
因此,我们再去看蒋在的告别宣言,就更能体会到其中的郑重与勇气。异域性写作已带给蒋在诸多的认可与荣誉。按说,在竞争激烈的青年作家群体中,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与风格,会更容易“出人头地”,这也是当下的时代逻辑——被归类与被标签,如网红博主集中在某个领域创作会得到更多的曝光与流量。作家能主动拒绝被标签的诱惑,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告别向来是艰难的,然而这又是成长无法避免的。
从《街区那头》到《飞往温哥华》,我们可以读到蒋在的飞跃性的突破与成长。在前者,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蒋在那颗诗人的灵魂在跳跃。蒋在似乎被他乡的孤独所淹没,浓郁的情绪挥之不去。到了后者,蒋在终于将自己抽离出来,较为冷静地观察温哥华、观察自我。诗人的灵魂隐藏在克制、冷静的文字背后,只偶尔显露出来。她在用小说的声调叙述,而非用诗人的声音在抒情。
在《文学报》的访谈中,蒋在谈及转变的原因,是“从异国他乡回到一个我熟悉又不那么熟悉的故土重新开始生活,必定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另外从校园步入社会,一个人承载的身份会更多——工作者、北漂、女性、女儿、妻子、母亲等等,这些身份会随着时间逐渐开始叠加”。简而言之,作家需要成为一个更为丰盈与充沛的个体,同时,也需要更大的勇气去回答关于自我、社会与时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