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白杏珏
5月13日,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丽丝·门罗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家中逝世,享年92岁。
对我来说,作家逝世的消息,总是显得有些遥远。因为我是从作品里,建构起对作家们的感知的。而当作家的肉身逝去时,那些曾经翻阅过的书籍还在我的手边,那些曾经咀嚼过的字句还在我的心里。我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离去呢?
但艾丽丝·门罗却不一样。在她去世的这个五月,我刚开始阅读她的作品《爱的进程》。此前的三个月,我和朋友们一起陆续精读了《你以为你是谁?》《公开的秘密》等作品。甚至,在她去世的当天晚上,朋友们还在微信群里进行了一次精读讨论。这种因缘巧合,这种尚且新鲜的阅读体验,让我觉得她的逝世变得如此真切。
如此真切,就像她笔下的生活。门罗不能被概括为“当代的契诃夫”。这样的类比,只是将当代作家纳入经典文学序列的一种简单尝试。门罗作品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她不是契诃夫,也不是莫泊桑。她书写的,是近一百年的生活,尤其是这一代女性的生活。她所描绘的一代人,是我们的当代人。也正是因此,门罗会在中国的年轻女性群体中收获如此多的读者。她们亲切地称呼她为“门婆”,就像称呼一位身边的女性长辈。
女孩,少女,女人,女性;女儿,妻子,情人,母亲。 92岁的门罗走过了自己的一生,并用那些精心编织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其实远没有理解我们所经历的生活。

年轻时的门罗
一 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样重要
纪念一位作家,似乎避不开回顾生平。艾丽丝的人生,有点像她的名字,是一个偶然跃入兔子洞的女孩的一生。
1931年,艾丽丝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西南部的小镇威汉姆。她有一位雄心勃勃的教师母亲,一位热爱户外的农民父亲。她的父母一起努力经营着一个农场,勤勉地做着步入中产阶层的幻梦。但这个梦想,很快随着母亲的帕金森症而一败涂地。艾丽丝从小就喜欢编故事,也秉持了小镇青年的刻苦精神,顺利考入西安大略大学新闻系学习。她离开了穷困的小镇,接触到中产阶级的生活,并在大学第二年退学,与家境优渥的詹姆斯·门罗结婚,获得了“门罗”这个姓氏,以及看似轻松实则忙碌的主妇生活。她与詹姆斯生育了四个孩子,一个不幸夭折。她养育了三个女儿长大。
她利用一切时间写作。她与丈夫渐行渐远,有过一些浪漫韵事。她不断地写,获得各种文学奖项,逐步扬名北美乃至世界文学圈。她离了婚,与校友弗兰姆林再婚,住进了小镇。2012年,她出版《亲爱的生活》,并宣布封笔。那时,她已年过80岁。2013年,她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诺贝尔文学史上首位加拿大作家。2024年5月13日,她在92岁的高龄去世。
就像许多作家一样,门罗生前常被询问:你与你笔下的人物,有多大的相似之处?人们总按捺不住探寻作家生活的冲动,因为将躲在幕后的作者拉到舞台前,盘问出一个清晰明确的“真相”,实在是一件太诱人的事情。
对门罗而言,这个问题更是难以规避。因为她的个人经历与作品的相似程度,是如此显而易见。就以《你以为你是谁?》为例,这部门罗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以一位女孩露丝的人生为线索,写了10个短篇故事,每个故事对应露丝的一个成长阶段——被父亲鞭打的小镇女孩,向往“校霸”生活但处处小心谨慎的中学女生,犹豫是否要嫁给富裕男友的“乞丐新娘”,意外出轨朋友的已婚妇女,被年轻男孩诱惑的大学老师,以及面对继母(母亲)的衰老病弱的中年女儿。读者很容易在她的作品与人生经历间找到诸多关联。
但门罗不是自传性的作家,她更感兴趣观察分析别人的生活。她不是安妮·埃尔诺,也不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确,门罗的作品离不开她曾经生活过的小镇,也离不开她“小镇少女”的成长体验。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真实”为她吸引了许多读者。但是,正如她在接受采访里所说的,“书里所描绘的情感,都是我真实经历过的。但故事不是”。她只是依据自己真实体会过的情感来创作故事,跟大多数作家一样。
故事的“真实”,不是事实意义上的“真实”。好的故事,是一种比现实更真实的生活,因为它包括“可能发生的事情”。如诺贝尔颁奖词所言,在门罗的故事里,“可能发生的事情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一样重要”。她笔下的人物,总是在念想着另一种生活:嫁给“富二代”的小镇女孩想着,如果当初她坚持拒绝了那枚钻戒;囿于家庭的主妇想着,如果自己在那辆逃离的汽车上再多坐一会儿;被邻居侵犯的女孩想着,如果当初有人能回应她的呼救;与小镇企业家结婚度过一生的图书管理员想着,如果当初那个从战地给她写信的男人没有被意外杀死……而且,这种念想往往是回望式的,是一次次遥远的叹息。
人心之所以复杂,正在于那不断翻新的念头,那无穷无尽的关于可能性的想象,那在回忆中反复默念的“如果那样……就好了”。这种可能性,是虚构与非虚构的分界。现实的生活与可能的生活交织,才是一个好的故事。如鲁迅所言,好的故事,就是在朦胧中,坐上一只小船,看见的一片“永是生动、永是展开、看不见结束”的倒影。正当作者要凝视的时候,那篇倒影就碎了,而人也不在小船中了。优秀的作者会努力打捞这些碎影,并尽力编织成一个理想的整体。但在他/她的脑海里,永远有那一片在昏沉的夜里,不断变动的倒影。
门罗的故事里,就有细密编织的碎影。她的故事里往往布满了细节,等待着读者去发现:一个鬼脸,一顶帽子,一次沉默。而她也总会在故事的结尾处,带着我们一起望向那片永恒的倒影。在《真正的生活》里,门罗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强壮而内向的女猎人多莉,与哥哥阿尔伯特一同居住在农场。哥哥死后,她遇见了一位喜爱打猎的外国富豪,并在闺蜜米莉森特的劝说下,接受了求婚,搬离了生活已久的老屋,去往国外。婚后的多莉看似过上了女王般的生活:在广袤土地上种植作物,骑马,开飞机,周游世界,最终死于登高看火山的过程中。
多莉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女性形象。她孤独而强大地生活,并成功地完成了“逃离”。但是,这就是所想要的生活吗?门罗在小说结尾,用充满诗意的笔触再现了一个动人场景:“每年秋天,多莉会和哥哥一起收集树上落下的核桃,一个一个地数,将数字记录在地窖的墙上,然后把它们倒在田埂边——充满了习惯的生活,季节轮换的生活。核桃从树上掉下,麝鼠在小溪里游泳。多莉一定相信她本该如此生活,连同她那合情合理的古怪,可以忍受的孤独。”
当我们望向那棵秋日的核桃树时,我们也就望向了属于多莉的,也属于我们的,人生的倒影。
现代性的危机,在于信仰被动摇后的茫然四顾。人们无法确证自己的生活,并惊奇地意识到,人生的许多关键转折,可能只是起于一个莫名的闪念。门罗笔下的人们,留守者在遥望,逃离者在犹豫,出走者在回首。门罗不会给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她只是如实地描述现实的生活和可能的生活,并轻声告诉我们:或许,我们期待的只是看清那片永恒的倒影。
二 女人们的秘密
门罗曾说:“我从来不知道‘女性主义’(feminism)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不过我的确是个女性主义者(feminist)。”谈论门罗,女性主义必然是核心议题。
其实,当我们用“门罗”来指称“艾丽丝”时,就已经触及了女性主义的问题。门罗是她前夫的姓氏,为什么不改姓?这是一些年轻读者好奇的问题。
首先,改姓会带来很多生活上的麻烦,艾丽丝不是一个喜欢自找麻烦的人。其次,改姓只是一个看似激烈的反抗动作。这个姓氏代表的是她所经历的一段人生。而门罗不会轻易地否定任何一段人生。她只是会不停地问:一定会这样吗?如果是另一种生活,又会怎么样?
门罗的女性主义,并不在于简单的攻击和否定男性。初读门罗,会容易有这样的误解。她以相当敏锐,甚至可以说有些残酷的笔触,刻画了许多面目可憎的男性形象——怯懦的,自大的,幼稚的,暴力的,性欲旺盛的,自吹自擂的,无力直面生活真相的。例如,在《苔藓》里,她便以相当精准的方式,描写了一位以追逐不同女性为乐的中年男子大卫,并一语道破其“只是长不大的男孩”的本质。她还冷静地展现一些男性犯下的罪行,大部分与性欲和暴力有关。
可门罗也以同样的敏锐在剖析女性各种幽暗的心理,她的写作是批判性的,总是在不断审视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只不过,她对笔下的女性角色多了几分温柔,那是一种母亲对女儿般的女性温柔。她知晓女性的缺点:虚荣的,胆小的,犹豫的,逃避的,容易被爱情欺骗的。但她总怀抱着温情,因为她知道这些缺点,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社会环境乃至文学话语的形塑。于是,她为这些女人们设计了一种尚且可以接受的人生,就跟她自己的人生一样。平凡,但是安全。然后,门罗为她们打开了一片幻想的天地,那是自由呼吸的场域。
这是一种厚此薄彼吗?横向来看,或许是;纵向来看,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认真回顾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命运,会很明白地发现,许多经典作品中的女性命运是过于残酷的。这种残酷,在某种意义上,源于作者对角色的不在乎。以出轨的女人为例,人们所熟知的经典文学形象,是在无尽的自责中,奔向绝望死亡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坦诚地说,文学序列里的包法利夫人已经足够多了。21世纪的读者,确实需要读到一位露丝女士,她之所以被一个拥抱引诱而想到出轨,只是因为她“想要小花招,想要闪着金光的秘密,想要温柔的爱欲”,而当她发现对方只是将这件事说成“淘气”时,她无法冷静,在深夜打电话,但没有获得想要的回应。最终,她的生活也就继续了下去。
女性的生活,是公开的秘密。这世间有许多女性过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生活,这些生活如此真实,但还未充分地被书写,甚至被言说。而门罗的女性主义,就是不断地替所有未发声的女性,讲述她们生活中那些微妙的时刻,并将这些女性的秘密镌刻在经典文学序列中。《特权》里,女孩露丝要送糖果给学校里的“不良女孩”科拉,因为她崇拜科拉在面对一群男孩的挑衅时,能毫不留情地大声咒骂。《野天鹅》里,少女露丝在火车上遇到了陌生人的性骚扰,而她没有立即呼喊的原因是不理解,是害怕,是犹豫,也是年少的无知与好奇。《忘情》里,年老的露易莎在幻象中看见了那位素未谋面的爱慕者,向他讲述了自己婚后“正常的生活”,并惊恐地发现那个人的面目变换不定。《公开的秘密》里,莫琳似乎发现了镇上少女失踪案的真凶,却没有说出,只在脑海里惩罚了他。
“虽然她已经朝公开的秘密张望,但当你尝试开口讲述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它多么惊人。”冷静地讲述现代社会里,那些公开的、惊人的、与女性有关的秘密,不断地塑造并且丰富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这就是门罗式的女性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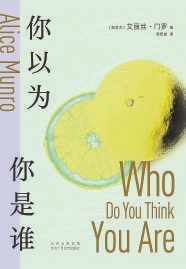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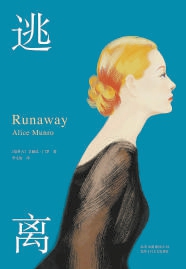
门罗部分作品的中文版
三 一只猫走过餐桌
门罗的写作风格,承袭了海明威开创的北美短篇小说的传统。结构完整,聚焦个人生活,揭露冰山下的一切,文字力求简洁、精确。那么,门罗到底做到了什么程度,使得她从一众北美作者中脱颖而出呢?诺奖颁奖词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阅读她的一段文字,就好像看着一只猫,走过摆好餐具的晚餐桌面。”这很适合描绘门罗的文字特点。
且举《忘情》(Carried Away)里的一段文字为例:
上周五早上,道兹工厂的锯木车间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悲惨事故。杰克·阿格纽先生在将手伸到主转轴下面时,衣袖不幸被法兰盘上的定位螺丝扯住,他的胳膊和肩膀被连带着卷到了主转轴下。他的脑袋随即碰到了直径约为一英尺的圆锯。这位不幸的年轻人立即身首异处,他的头从左耳下方的脖子处被削下。他被认为是瞬间丧命,来不及发出任何呼叫。因此,让工友惊觉这场恐怖灾祸的不是他的声音,而是从他的身体里喷溅而出的鲜血。(张洪凌译)
这段文字,描绘的是一次可怕的事故:一位工人因机器意外而被斩首身亡。门罗在这里戏仿了加缪式的新闻报道风格,在异常精确地描写了一个堪比恐怖电影的事故画面时,更巧妙地讽刺了旁观者对于此类事件的态度。这是一段嵌合精美的文字机器,每一个词语都在向着最终的悲剧推转。它告诉我们,这样的悲剧是与身体密切相关的。但对于旁观者而言,这场恐怖灾祸没有任何声音。他们看到的往往只是喷溅而出的鲜血。他们会说,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悲惨事故。但他们不会看到真正悲惨的细节。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门罗在这段文字前,又点出了杰克所在工厂的制度标语——“安全问题,切勿大意。当心自己,留意工友。”在这样的制度里,工人的安全只能依靠自己的“切勿大意”。而工厂老板阿瑟,在日后解释这场他亲眼见证的事故时,也体现出了与标语一样的、高高在上的、资本主义式的冷漠:“并不是机器拽住他,跟野兽一样把他拽了进去。他操作失误,也可以说是不小心。然后他就完蛋了。”这几段文字,被编织进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爱情与婚姻故事里,体现出了门罗出众的阶级意识。她严厉地指出了资本主义逻辑的可怕之处。但不同于理论家的分析,作为一名小说家,她是通过具象的场景来呈现这一恐怖景象的。
门罗的精确,在于她对人性的准确把握。她最擅长通过一些细节,瞬间揭露人性的褶皱与缝隙。她写固守传统观念的已婚妇女米莉森特,会说米莉森特认为女猎人多莉是“通过拿刀叉的方式捕获了那个男人的心”,因为这是最接近淑女的表现。她写大龄未婚的音乐教师缪丽尔,会写“她总穿蓝色的衣服。她说女人应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颜色,然后就只穿那一个颜色”,因为许多女性总会以自己的审美为骄傲,并相信这是一种个人价值。她写小镇女孩露丝第一次来到男友家的豪宅,觉得“这里到处都会让人注意到尺寸,特别是厚度。”她写露丝从大城市回到家乡,觉得家乡人说话“词与词都是分开的,每一个都是重音,仿佛这样人们就可以用它们互相轰炸”。诸如此类的细节,往往是一句便勾连出一段人生,一种个性,一道鸿沟,让门罗的人物呈现出细腻的肌理,具体而真实。
门罗在小说形式上的尝试,也体现出精细勤勉的匠人精神。她一生都在磨炼写作的技艺,而从她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种螺旋向上的进步。她最精彩的一部分作品,就是她创作中后期,那些经过反复锤炼后,结构与内容臻至完美的作品。作为一名不依靠外部力量变化,不依赖情节悬念反转的作家,门罗的优势在于敏锐而具有批判性的人性剖析,而她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种“情绪的室内游戏”变得引人入胜。或许,在这个意义上,她与契诃夫有一定的可比性,契诃夫同样不是在情节上取胜,而擅长探寻人性的幽深与情感的绵延。她的行文虽然节制,却有着相当强的言说欲。作为一名作者,在作品里,她的声音是时刻在场的。这是她的优点,但如果作者那睿智而冷酷的声音过于突出,就会像是交响乐演出里张扬炫技的小提琴独奏,精彩,但会让观众从整体氛围里抽离。
在门罗的早期作品里,这种内与外的拉扯,作者言说与读者接受之间的距离,还是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而当成熟时期的门罗,找到那把扭动机关的钥匙时,一切就能自然而然地运转起来。这个时候的门罗,会更加在意读者的阅读体验,而非自己的表达欲望。在她熟练运用书信、悬疑、侦探、浪漫小说、民间传说、维多利亚文学乃至科幻小说等形式文体时,她将这场表演变得更适宜于大众观看。就像一只灵巧的猫,它自如地绕过桌上的餐盘,是因为它的天性禀赋;但那种赏心悦目的优雅,却来源于周围观看者的目光。
在这方面,《荒野驿站》等便是相当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门罗在文本形式上的精彩实验,也是纯文学与类型文学融合的写作样本。《荒野驿站》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和当代美国黑色犯罪电影的奇妙融合。若是概括故事情节,这是一个科恩兄弟会乐意拍摄的悬疑故事:19世纪50年代,某孤儿院院长将院内一名孤女安妮嫁给了在卡斯泰尔斯拓荒的男人西蒙。这名拓荒者脾气暴躁,固执己见,有暴力倾向,与自己的兄弟乔治一同在荒野里搭建了小屋。女孩来到小屋之后的早春四月,西蒙与乔治出外伐树。等乔治归来时,安妮发现西蒙已经死亡。之后,这个秘密永远地改变了安妮的一生。
门罗采用了书信体的形式,通过不同人物对这件事、对其他人物的回忆与猜想,编织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门罗的高超技巧,只有阅读过原文本才能体现,我只需指出一个事实,就是这篇看似罗生门式的故事,只有不到40页篇幅,但在时间上跨越了一百年:第一封信由孤儿院长写于1852年,最后一封信由老安妮的雇主女儿写于1959年。在这40页里,是一个升级版的“简·爱”故事:孤女安妮在风雪夜见证了死亡。她被当做疯女人乃至凶手,被关进了监狱。她曾经天真、惶恐、无知、轻信。但最终,她成长为了猫一样诡谲神秘、无坚不摧的老安妮,并最终完成了迟到的复仇。
《荒野驿站》有点像“大女主爽文”,阅读体验类似看韩剧《黑暗荣耀》,几乎是一气呵成。这是门罗在作品可读性上的成功尝试,但这部小说无疑有着远超通俗作品的价值。这种价值一方面是技巧上的纯熟,也就是门罗作为“形式大师”的表演。另一方面,在于它重新书写了“简·爱”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名孤女终于在磨难中尽情成长,不借助婚姻或爱情的力量,不借助圣母光环或纯真善良,独自面对并走过坎坷的一生。
门罗获得诺奖后接受采访,曾回忆过自己童年的一个故事。她说,当她小时候听人讲述小美人鱼的故事时,她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她不能理解小美人鱼在付出那么多的痛苦之后,还会是那样的悲惨结局。她想要重新讲述小美人鱼的故事。
艾丽丝成功了。那些她笔下的女性们,不再轻易地化作泡影,而是迈着猫一样灵巧又莫测的步伐,走完了属于自己的百年孤独。(白杏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