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三 心
挪威作家达格·索尔斯塔的写作是静默的潜流,没有华美比喻的浪涛,没有繁复句式的漩涡,没有以佶屈聱牙的晦涩构筑段落的航道。他的小说集《安德森教授的夜晚》包括《羞涩与尊严》和《安德森教授的夜晚》两部中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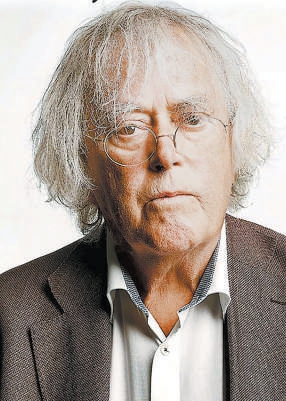
挪威作家达格·索尔斯塔
主人公都是孤独的人
在《羞涩与尊严》的开头,他轻描淡写高中教师埃利亚斯“轻微有点酗酒”这一引人遐想的习惯,用一种以叙事者语言包裹人物想法的技巧,描述日常“他和自己稍嫌臃肿的太太共进早餐”。“稍嫌臃肿”这个形容让读者轻盈地把握住了教师的隐匿思绪,关键性的道具不着痕迹自然出场——“如果下雨也不奇怪,他想,拿起他的折叠伞”。跟随叙述的延展,读者会意识到小说涌溢着一种流动性的文风,达格·索尔斯塔的笔触不再流连忘返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静物式的描写。心理抑或叙事都似乎不可阻挡地行进,看似缺乏技巧张力的句子却骚动着一种宿命感。人物的思绪在两篇小说中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羞涩与尊严》中除了必要的对话,引号被弃置,现实描述和心理意识被看似漫不经心地用独特的节律平摊在一起,娓娓道来的陈述语调触动着读者心弦。在《安德森教授的夜晚》中则反其道而行之,引号喧闹地跳动,类似于“他想”这样的信号明亮地跳跃着,时刻提醒着读者这个人有多么沉溺于自己的意识,而一个沉溺于自己意识的人又怎么能不是孤独的呢?
本质上,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孤独的人。比如他们二人强迫症般诡异的仪式感。他们沦陷于生活的困境中,用某种带有僵化的仪式感但实际上并无意义的事情进行安慰式的调和。约翰·多恩有一首诗名为《无人是孤岛》,但对于达格·索尔斯塔笔下的人物而言,无人不是孤岛。埃利亚斯能引起读者真切的同情,因为他不仅是个孤独的人,而且是个孤独的好人。他虽然是一个好人,但无法实现他最简单朴素的愿望,说白了,他无法理解生活。小说的语言是永不停歇的航行,但人物没有指引的地图。埃利亚斯有迷惘、有混乱、有私欲,但这一切被生活的洪流淹没。他深感自己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人物的命运和叙事的延伸则同样随波逐流。孤独无法共振,孤独只能彼此孤独着。小说有这么一个孤独极端膨胀的时刻:埃利亚斯听到了一个非以文学为职业的数学老师,不经意地提到了托马斯·曼《魔山》中的一个人物,他讶异于这个时代还有人真的会去读那些课本之外的文学作品。他着魔般地想去和他交谈一番,但在社会规约的桎梏下,他根本找不到契机,在无望的努力后只能作罢。
孤独感的渗透方式
埃利亚斯那“稍嫌臃肿”的太太埃娃·琳达则被埃利亚斯的视角一直检视着,这个局限的视角无法探索到人物的深层,但读者会更加觉得这个人物有着某种深藏不露却独属于自己的哀伤。当琳达向奢侈品橱窗流露出贪婪的目光时,读者和埃利亚斯一样,对她有了焕然一新的认识。埃利亚斯从他自身的视角出发,感到惊骇,因为这时他才意识到这是“她对自己生活的真实表达”;但从读者的视角而言,一直躲在暗处的人物此时变得鲜活起来,不再如同表面看起来那样被动地黏贴着生活。被毁灭的不仅仅是埃利亚斯的生活,也有琳达的生活——小说不再只有一个陈词滥调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男性白人的自白与抱怨,在此处,小说缄默地哀悼着一个同样被生活摧毁的女人的命运。
在中篇小说《安德森教授的夜晚》中,孤独感渗透的方式不再是一种强力的情绪渲染,相反,小说开始的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可以称得上轻松的语调。即使他目睹了一起杀人事件,小说的基调也并没有突变为深沉的控诉。他目睹的杀人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一个小小的实验。虽然作者用一种尽量贴近生活的语言来叙述,这偶发的事件还是散发着不真实性——毕竟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社会环境中,很少会有人真的“有幸”目睹一次谋杀事件,更遑论还和杀人凶手进行了一番偶遇并结识交谈。于是,小说表现得像一场即兴的实验——作者即上帝,这场实验的目标就是探测意识的深不可测。也因为是实验,我们与作者同时站在命运之山俯瞰人物思绪的紊流。小说洋溢着喜剧性,虽然这对人物本身而言是猝不及防的无妄之灾。随着叙述的深入,读者越来越不在意安德森教授什么时候向警方告发,相反,我们期待他继续围绕着原地打转,期待看到这种深不可测的意识究竟还能让他做出何等啼笑皆非之事。叙述不营造任何紧张感而徐缓地漂流。
文学越来越不像文学
这两篇小说共享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当代知识分子之殇,其根源是古老而沉重的“文学之死”。人物之间无法产生真正的灵魂交流,反而是人物与文学之间可以炽热地结合,但这种结合无法在真正意义上传递给他人,文学的光芒最闪耀之时就已经注定了黯淡的结局。文学越来越成为不像文学的东西,沦落为被顶礼膜拜的死气沉沉,如同落满了尘埃与蛛丝的神像。但神像同时也意味着远离人间烟火的疏离感,人们不再去谈论文学,刻意地避而远之。如果一个作品无法对读者的心灵发动地震,那么作品的意义何在?问题是,作品和读者的关系是封闭式的,心灵共舞只能局限于两个人。
安德森教授为什么不去报警?这与他对所身处社会的态度有着暧昧的关联,这种焦虑是放大了的生活缩影。他对文学的疑虑和他对报警的疑虑都有一个共同的落脚点,就是他自身的价值观如何融入社会。他深知从道德角度而言他应该去报警,但他已经成为一个怀疑论者,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两者在他的心中不断交战,他渴望置身事外,就像他希望能置身于社会之外一样。这种怀疑也让《安德森教授的夜晚》比《羞涩与尊严》在关于文学性探讨的道路上奔驰得更远,因为他甚至对文学所引发的心灵震颤也产生了怀疑:“人类创作的艺术作品从未产生过这样的震撼。它们只是凭借其当代性引起了我们的共鸣,但没有能力超越那个界限。”《安德森教授的夜晚》也没有超越那个界限,但达格·索尔斯塔对这种界限施展了悖论性的魔法:他通过对“文学性不再引发心灵震颤”的质询打动了读者,让读者产生心灵震颤。我们的心灵震颤是因为我们发现自己对心灵震颤产生了怀疑。我们也变成了和安德森教授一样的怀疑论者。或许,文学就如同那个杀人凶手,是具体的存在,扰乱了我们意识的船桨。有朝一日,读者和文学也会像安德森教授和杀人凶手一样在命运的安排下相遇。
(作者系书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