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洪治纲
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文化就像血液一样,维系着我们的生命,并最终证明我们此在的身份、气质与襟怀。唯因如此,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感召之下,各种有关历史文化的反思性重述,几乎成为当代散文发展的主脉。这对于我们重新打开历史记忆的褶皱,寻求自我生命的精神之源,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审美的自觉,王国益的散文也常常聚焦于传统文化,以丰沛的主体情感激活各种历史文化元素,又以文化探幽者的姿态抒发创作主体的生命情怀。即使着笔于山水城乡之景,王国益也会踅进深厚的传统文化肌理之中,辗转盘旋。这集中体现在他新近出版的《王国益散文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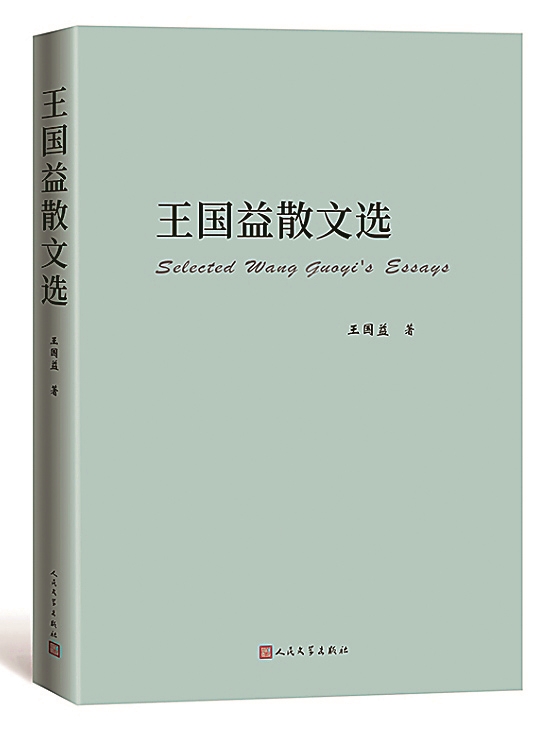
或许是长期生活于江南的缘故,我读《王国益散文选》,既备感亲切,又时觉陌生。说亲切,是因为除了北方的台儿庄以及少数域外之城,这本散文集中的不少篇章所游之景地,或所叙之人事,是我所熟悉的,特别是西溪湿地、西泠印社,以及烟雨西湖,更是我携朋唤友的常游之处。但我又常感陌生,因为作者总是曲径探幽,援古谈今,很多历史褶皱里的文化事象,都被他娓娓道来,让我甚为讶异,像《前川梦吟》中所述义乌凤林王氏始祖王彦超、《跌宕人生两度春》里的王龙泽等。如果说有关凤林王氏家族太祖贤宗的书写,是基于王国益对自身先辈的礼赞与敬畏,包含了某种历史的荣耀感,那么其他那些令人陌生之处,则更多地体现了作者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之情。
人们或多或少都有些历史意识,都能够通过回忆,将时间经验转化为生活实践的导向。凭借历史意识,人们可以从不同维度认识到自身变迁的内在逻辑,从而将历史理解为一种具有内在关联的连续性发展过程。王国益的特殊之处在于具有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散文看似游记,但在移步换景之间,都是对历史文化的缅想。他不是“历史的”而是“历史地”看山看水,既体现了作者承传历史和建构历史的潜在动机,也表明了他试图借助过去阐释现在的主体自觉。在《百年印社何辉煌》里,作者梳理了西泠印社120多年的历史,居然有一半时间没有社长。盖其因,是该社对入社成员及社长,均有极为严格的自律性要求,特别是作为掌门人的社长,必须是一座艺术高峰,且能展示印社之魂。许多篇目都体现了作者超越一般人的认知局限,沉入历史的内部,从不同的文化维度,形成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这种历史意识的自觉,使王国益的散文有效颠覆了游记的特性,变成对历史文化的打捞、梳理与重释。“西溪且留下”的典故、康熙南巡题诗《题西溪山庄》并御书“竹窗”的故事,还有洪园的历史变迁等不为一般大众熟知的历史往事,正是一个地方的文化之魂。没有这些人文的魂魄,那些所谓的景点不过是一些自然地理,虽有奇观,终究少了些神韵。如《中华奇庄》里,作者从传说中的奇人异事写到汪塘的商贾云集,从青楼里的传奇韵事写到抗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令人对这座北方古城心驰神往。《积道山之蕴》从传说开始,从“神韵之山”到“不倒之树”,从“不竭之井”到“聪慧之人”,一路叙述下来,或山或树,或井或人,皆渗透了中国人的生命智慧,也洋溢着江南的文化灵性。在这些散文中,作者通过“自然—历史—文明”的叙事逻辑,将特定的地理空间提升为传统文化的符号载体,既体现了作者对华夏大地的生态礼赞,也折射了作者对民族精神与历史传承的现代诠释。
这无疑是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文化情怀,凸显了作者内心里的人文禀赋。在王国益笔下,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词频繁出现,那就是“神韵”。神韵就是神采韵味,既透示了特殊的精神气质和格调,又饱含了某些难以言说且真实存在的美感,并吸引人们去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王国益钟情于这个词汇,显然领会了其笔下所叙之事物的生命气息。他总是以文化寻根为经,以情感哲思为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编织出各种充满张力的生命图景。如《百年印社何辉煌》中,他将西泠印社的篆刻解读为“刀尖上的哲学”,“刀痕入石三寸深”的篆刻技艺,被赋予“在时光中镌刻永恒”的哲学意味;金石篆刻的“留痕”,寄寓了作者对生命“留痕”的执念。《神韵的故乡》里的“老井”“族谱”“戏台”等意象所构成的文化符号,每个意象既是具体可感的物象,又是传统文化密码的载体。《积道山之蕴》中山顶上的那棵千年古树,从“皴裂的树皮”到“虬曲的枝干”,每个细节都是情感密码的载体。这种物我交融的审美观照,使自然意象成为打开集体记忆的钥匙,实现了个体情感向文化共情的转化,也使个体生命的琐碎细节,在文化经纬中编织出文明的锦衣,折射了作者生命深处的文化情怀。
这种从生命深处涌出的文化情怀,很多时候都成为作者理想人生的隐喻、民族精魂的寄托,展示了创作主体灵魂深处的精神追求。在《百年印社何辉煌》里,作者从篆刻中看到,“刻印如修身,雕琢似齐家,给石头以人格,赐玉石以品行,镌田墨以灵性,方寸之间,降服人心”,深切地体悟到“一支铁笔镌世界,半方石印藏乾坤”的伟岸境界。在《露易斯湖的追思》里,作者由露易斯湖的美景一路追踪,叙述了崇尚自由与博爱的路易斯公主,由此联想到中国古代的解忧公主与乌孙国的联姻,以及华人对加国铁路大动脉建设的巨大贡献。在《风雨潮头读浙商》中,作者从浙商的历史血脉中探讨精神源头,其中既有来自良渚、河姆渡的“先祖文化”,多山少地、辗转艰难的“土狼文化”,又有忍辱负重的“耕牛文化”,以及搏击海浪的“海鸥文化”。正是它们,成就了今天这支兼具“草根精神”和“文化贾儒”的文化商旅。在《闪光在中国》里,作者从白求恩的双重人格里一路追述,通过立体化的性格探秘,展示了这个医术与理想极为高迈的灵魂。在《婺州不灭之光》里,作者追述了金华北山四先生闭门苦读,广设书院,不入仕途,礼赞了他们成为千年不灭的儒学精魂。王国益的散文,既延续着中国散文“载道”“言志”的古典传统,又熔铸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情操,并形成了个性鲜明的艺术品格。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激荡的今天,王国益的散文无疑提供了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珍贵样本。他的创作实践,表明了传统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被重新诠释,也证明了文化记忆的保存,不应是博物馆式的存列,而应是植根于不同灵魂中持续生长的生命体。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