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彭忠富
琉璃厂的雪天访书、圆明园的塔下寻珍,以及与谷林、锺叔河等文化人的交往剪影,在古朴细腻的笔调中交织成一曲关于书缘与人缘的抒情长调。散文作家朱航满的《一枕书梦》是一部围绕“书”字铺陈的书话随笔集,收录了《鲁迅故居买书记》等41篇文章,恰似一轴徐徐展开的文人画卷。其实,最好的书话就是人与书、人与人间的灵魂共振。这种共振,让《一枕书梦》超越了个体经验的局限,成为一代人关于读书、关于文化、关于精神家园的集体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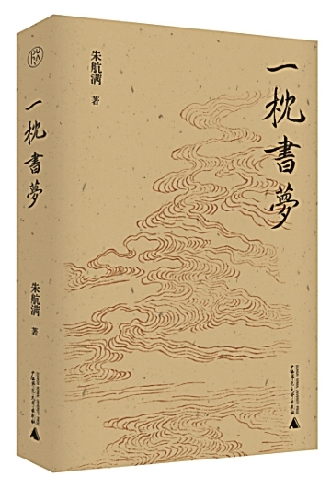
朱航满对书的痴恋,首先体现在对“书缘”的深情追溯。他笔下的购书经历,既是个人阅读史的注脚,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雪天访书》中,琉璃厂的雪色与古籍的墨香浑然一体,“万松老人塔在雪雾中若隐若现,旧书店的木门吱呀作响,宣纸封面的线装书在台灯下泛着温润的光”,这般场景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还原,更是对传统购书方式的诗意重构。在地坛书市的摊位前,他偶遇1991年版《知堂小品》,扉页上“1994年十月五日新源里中国书店”的题跋,让一本旧书成为跨越时空的媒介,连接着三代爱书人的体温。
《一枕书梦》最动人处,在于作者与文化名人的交往书写。这些文字不似史料般冷硬,而是带着体温的精神对话。谷林先生的“知己自在万人丛中”,锺叔河先生编选《念楼话书》时的严谨与温情,孙郁在鲁迅博物馆的深夜长谈,都在细节中见出文人风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边缘文人”的关注,如翻译家吴钧陶、学者陈乐民,他们的著述与性情在作者笔下复活,成为当代文化图景中不可或缺的拼图。
作者对师友的追忆,始终浸润着谦敬之心。回忆导师陆文虎先生,他没有堆砌溢美之词,而是通过“先生书房里永远摊开的《管锥编》”“修改文稿时用红笔标注的蝇头小字”等细节,勾勒出一位学者的精神肖像。与布衣书局创始人胡同的交往,则见证了民间书业的兴衰:“那些在冷摊前翻检旧书的时光,那些与书贩讨价还价的烟火气,都是爱书人难以割舍的江湖。”这种将人物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书写,让“人缘”成为流动的精神血脉,在代际传递中生生不息。
朱航满的文字风格,可用“古朴清明”四字概括。他摒弃了时下流行的炫技式写作,回归中国传统散文的“简笔美学”。写逛旧书店,不过“冷摊前蹲下身,指尖拂去书脊的灰尘,忽见某页夹着半张泛黄的戏票”;记友人赠书,仅是“信封上的钢笔字工整如碑帖,拆开时飘落一片香山红叶”。这种克制的抒情,恰如周作人所言“煮豆微撒以盐”,于平淡处见真味。
书中对北京古迹的描写,更显文字的诗性特质。鲁迅故居的“青瓦白墙间,几株丁香开得正好,树影在窗纸上摇曳,仿佛当年周树人握笔的剪影”;圆明园遗址的“断壁残垣间,野草丛生,某块石碑上的‘长春园’三字,在暮色中泛着幽光”,这些文字不是简单的景物速写,而是将历史沧桑融入个人感知,形成独特的“文人地理”书写。正如孙郁所言:“他的文字像深夜里的笛声,幽玄而清新,驱走独处时的寂寞。”(彭忠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