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陈秋实
1900年,一名年轻的西班牙画家抵达巴黎;1973年,他以“现代艺术巨匠”之名,在法国南部离世。他在法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却始终未成为法国公民,只有一份法国警局编号“74.664”的“S”级档案,默默记录着这位“异乡人”——毕加索在漫长岁月中的挣扎与选择。法国作家安妮·科恩-索拉尔的新作《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正是抓住了这段尘封的历史往事,揭示出毕加索如何在那个动荡年代,以画笔回应现实,一步步挣脱成见的重围,让世界重新理解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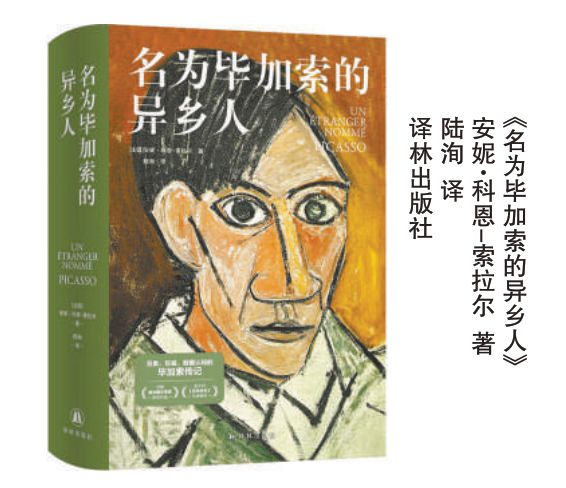
在巴黎的档案室与画廊之外,科恩-索拉尔的目光穿过了多年来笼罩在毕加索身上的传奇光环。她以法国警局档案为起点,还原了一个与主流叙事截然不同的毕加索——1901年首次巴黎个展前被警方登记在册,1914年近700幅作品遭扣押,直至晚年拒绝入籍法国。这些事件串联起的不只是这位艺术家的创作轨迹,更是一场长达七十年的文化身份拉锯战。审讯记录、居留证、入籍申请……这些冰冷的文件拼凑出法国社会对这位“外来者”的排斥与猜忌。毕加索并非被法国接纳的“艺术大师”,而是一个始终处于法国社会边缘的“异乡人”。初到巴黎的毕加索,多次尝试定居,却都以失败告终。他游走于充满暴力、野蛮又残酷的巴黎“丛林”之中,暗地里广交朋友,行踪不定,频繁更换酒店,以躲避监视他的人的骚扰。1904年,尽管已经在巴黎定居,毕加索也只能住在破烂不堪,如同贫民窟一般的“洗涤船”工作室里。但正是在这里,毕加索“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科恩-索拉尔的笔触并未止步于毕加索个人命运的沉浮。她将毕加索置于20世纪移民史、政治史与艺术史的交叉点,揭示其作品与那个动荡时代的深层共振。当《格尔尼卡》以扭曲的人体与破碎的线条控诉战争暴行时,它不仅是反战宣言,更是流亡者的集体呐喊。而当毕加索在战后法国政府的入籍邀请前沉默以对时,这种姿态本身便构成对民族国家叙事的无声抵抗。
书中更耐人寻味的,是毕加索晚年对巴黎的舍弃:他选择了南方而非北方,选择了外省而非首都,选择了做一名工匠而非学者。在法国南部的陶艺作坊里,这位年逾古稀的艺术家将神话、宗教与地中海的民间记忆揉入黏土。科恩-索拉尔将其解读为一场“归隐中的革命”。他不再追求画布上的永恒,转而拥抱陶器的易碎与质朴。那些粗粝的陶盘上,公牛、半人马与地中海女神在火焰中重生,既是对古希腊文明的致意,也是对现代性单一叙事的反抗。这种转向绝非逃避,而是以更激进的方式重构艺术的公共性:在地方手工艺中,他找到了超越国籍与边界的对话之可能。
《名为毕加索的异乡人》的突破性,在于它摒弃了传统艺术家传记对“天才神话”的沉迷。科恩-索拉尔耗费多年调阅法国国家档案馆、移民历史博物馆等机构的原始文献,让毕加索从艺术史的神坛上回归人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创作《亚维农少女》的革新者,更是一个为房租发愁的异乡客;一个因“外国人”身份屡遭针对的创作者;一个自从抵达法国,就被列入监视名单的“可疑分子”。这种祛魅的叙事反而让毕加索的形象愈发鲜活:他的艺术革命从来不是真空中的实验,而是在移民政策的夹缝、文化偏见的围剿中硬生生劈出的道路。
当作者将毕加索的“异乡人”身份与当代的移民危机、文化认同等议题并置时,这位艺术巨匠的形象陡然与21世纪的当下产生共振。在全球化撕裂又重组的今天,毕加索的选择提示着另一种可能:真正的归属感未必源于一纸证件,而可以通过对地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来实现。他晚年在地中海小镇的陶艺实践,恰似一道穿越时空的宣言——在20世纪的法国,当民族国家的边界日益森严时,艺术依然能够构建开放的精神家园。科恩-索拉尔在书中援引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的观点,将毕加索视为“世界主义文化”的先驱:他拒绝被任何单一的文化标签禁锢,转而将在“法国”和“外国”之间的游走转化为创作的养分。这种姿态,对于深陷身份焦虑的当代人而言,不啻为一剂清醒的良药。
作为一部艺术传记,本书的厚重不仅源于774页的篇幅,更在于其将个人命运与时代精神紧密编织的野心。科恩-索拉尔曾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长期从事跨文化研究,这使得她的叙事既具备档案研究的严谨,又充满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她笔下的毕加索不再是艺术史教材中的固定符号,而是一个在文化冲突的漩涡中不断自我重塑的“当代人”。当读者跟随文字走过毕加索的七十年异乡生涯时,也是在重新审视艺术与权力、个体与社会这些永恒命题。
合上这本书,毕加索的形象渐渐从那位手持调色板的天才艺术家转变为一个在地中海阳光下专注揉捏陶土的老人。尽管他的陶器看似脆弱,但它所承载的精神却坚如磐石。在困境与误解中,他选择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重新定义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一个如雅典“侨民”一般的异乡人。科恩-索拉尔通过冷静的档案分析与生动的叙事手法,还原了这一切,呈现了毕加索的另一面。这不仅是对毕加索的重新解读,更在不经意间与当下的我们产生了共鸣: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毕加索通过一生的探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或许这一答案就藏在那些布满指纹的陶器之中——归属,不是一个外界赋予的身份,而是通过不断创造与表达,逐步成就属于自己的“故乡”。
(作者为书评人、出版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