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张向红
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北京歌剧舞剧院制作演出、改编自陈彦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舞剧《主角》,本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该剧从70多万字的原著中提炼主线,讲述主角忆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皇后”的转折与蜕变,同时力图通过她的个人经历反映社会图景和时代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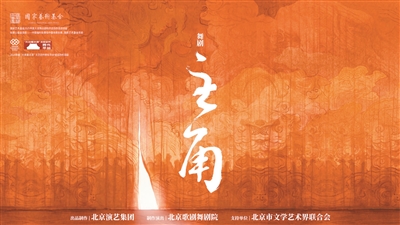
放羊娃百炼成钢最动人
先说动人的段落。
当易招弟改名易青娥(后又改名忆秦娥),当烧火丫头“入列”,成为秦腔剧团的一名学员,她的师傅胡彩香开始抽陀螺似的“炼”她。随着灯光的一明一灭、门的一开一合,硕大的舞台上,一束追光笼罩形单影只的易青娥,她手里的道具在不断变换,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器轮番上阵。
一个放羊娃要吃多少苦才能脱胎换骨?一个素人要泅过多少血泪交融的河流,才能站在舞台中央接受万千观众的检视与挑剔?而成为一代名伶又需要天地人怎样的成全?“哗”的一下,泪水就漫了上来——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不疯魔不成活……所有关于这一行的辛酸描述,通通涌上心头,通过这蒙太奇式的明灭开合,直击软肋。
这是剧中人忆秦娥的命运,也是此刻舞台上正在扮演她的年轻舞者正在经历的、一步都不能少的千山万水。
这一段的舞蹈动作也很好地融合了戏曲与现代舞这两种不同的范式,既有戏曲中手眼身法步的那个“范儿”,又未被拘泥,这之间的尺度拿捏得挺好。
可惜的是,女主何以从白丁一步步升级,最终成为秦腔的灵魂人物,其间的因果关系,再无浓墨重彩的描画,小人从中拨弄、男女情感纠葛等戏码成为此后的主轴。
狂热群舞对冲温吞主线
原著与舞剧都试图把忆秦娥“微观”的人生遭际与秦腔的兴衰、时代风尚的轮转结合起来,几场群舞承担了中观与宏观叙事部分,这几场群舞也不错。
第一场群戏表现非常时期的癫狂,低角度的灯光将舞者的动作放大数倍,映射在背景板上,狂乱不安的舞蹈与狂乱不安的剪影,寥寥几笔就交代了时代图景,笔墨精简写意传神。
另一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群舞是商品经济大潮初起,物资交流大会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热烈欢快活泼诙谐的板凳舞充分表现了三秦大地上的人们对秦腔的痴迷,土味十足的嗨曲《陕西愣娃一亮相》把气氛烘到爆棚——这种狂欢式的场面,对主线温吞拖沓的叙事节奏也做了很好的对冲。
当人们把锅碗瓢盆电器农具等一件件物资搁置于戏台,它们将唱念做打的主角一点点向后挤压到越来越逼仄的空间,此时此刻谁才是舞台上的“主角”已经不言自明——艺术,即使某个时刻可以全民为之癫狂,但终归难免它在社会生活排序中叨陪末座的尴尬,怎不令观者心中一声苦笑呢。

可惜只抡了个“半圆”
刚刚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又赴上海演出的舞剧《主角》,改编自陈彦的同名小说。作者在《后记》中说过一件事,当王蒙获悉他的创作主题时,这样鼓励他:“要抡圆了写,抡得越圆越好!”
那么,《主角》抡圆了没有?我以为只是抡了个“半圆”。小说《主角》的前半部大幅优于后半部;胡三元、胡彩香、“忠孝仁义”四位老艺人,甚至“反派”刘红兵等一干配角的塑造,都比主角忆秦娥更丰满细腻——这几乎已经成为《主角》读者的共识。所以,小说尽管得了大奖,但它有很明显的先天不足。它精彩的部分不断吸引着改编者,但它凹陷的部分也屡屡成为绊马索与陷马坑。甚至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主角》的每一次改编,都是对秦腔这个大IP的损害。
在文艺青年啸聚的豆瓣和年轻人活跃的小红书上,从小说到各种改编,都收获了很多犀利的酷评。据说,张艺谋任监制的电视剧改编已经在进行中,豆瓣已有相关词条。但从眼下的各种改编结果来看,即使张艺谋出手,也只能是谨慎乐观。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而舞蹈使用的恰好是语言之外的手段。曾有人批评《主角》小说“舟大水浅”,改编成舞剧剧本可以是一次去芜取菁大胆取舍删繁就简的机会。可惜的是,主创野心实在是不够大,他们几乎就是用舞蹈体裁把这个故事又重新复述了一遍,甚至在每一幕开始前,都通过字幕对人物关系、时代背景、故事梗概给予大段的文字说明。于是,也就未能弥补和跳脱出文本的先天缺陷。

角儿的境界哪是半推半就可得
小说最为人诟病的一点:从始至终,女主角忆秦娥都是从混沌中来到混沌中去,小说写她并不想唱戏,也不想演主角,只想跑龙套,屡次打退堂鼓。无论是对艺术的理解还是面对人生的种种困境,她始终都显得特别被动,仿佛完全是被外部力量推着走。
如果说,憨拙是一种难得的“钝感力”,可以把易招弟从一个无所知无所感无所谓的牧羊女,生拉硬拽地转变为职业演员易青娥,那么若成就大角儿,甚而至于成为某一个剧种的代表人物(所谓“秦腔皇后”云云),她严重缺乏内在驱动力、动辄退缩的被动性格,就完全没有说服力。
因为工作缘故,我也颇接触过一些戏曲界的“大姐大”,她们无论寡语还是善言,无论热烈还是清冷,只要略微走近,都会被她们强大的气场感染,甚至捕捉。那是艺术大家特有的魅力,也是百炼成钢者强大内核自然发散的力量感,难以言传但真实可感。
无他,戏曲艺术过于精深但又盛期已过,它极苦,极美,也极寂寞,能坚守并有大成就者,必有强大的精神内核。她们的境界绝非凡品,绝不是推一把进一步、就坡下驴顺势而为就可以抵达的。
一样是从懵懂痴愚走向蜕变,《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差可比拟。七连长高城就死活看不上三多,因为他虽然苦练死练,但他“只有兵的表,没有兵的里”;虽然他能拿到好成绩,但他没有血性,没有荣誉感。经过各种肉身与精神的双重磨炼,三多才一步步成长为真正的“兵王”。但忆秦娥的四十年,只有技艺的进步,没有心灵的成长,这也是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分近乎垮塌的主要原因——它没有说服力,很难得到读者的共情。
配角比女主更可爱
反倒是那些永远无缘C位的人物,比忆秦娥更有光彩。这次舞剧的呈现,也再现了这种失衡。
比如,虽然舞剧依原著保留了“忆秦娥与三个男人”的感情纠葛,但属于他们的佳章并不多。忆秦娥与刘红兵在各种家具之间闪转腾挪、追逐推拒,舞蹈设计尚有几分巧思,但与第二任丈夫石怀玉的双人舞则平平无奇,画家的形象甚至有一种油腻之感。
最有记忆点的双人舞反而属于配角胡三元与胡彩香。
这两个配角在“术”的层面是主角忆秦娥的引领者、托举者;在对待艺术的真诚、对待感情的执著等“道”的层面,更是拥有强烈的自觉。他们一个是打鼓佬,一个仅仅可以算作是女主角的开蒙老师,他们都没有机会站在舞台的C位,但他们远远比女主角更有信念感,无论是对自己热爱的事业还是认定的感情,都笃定不移,顺境逆境皆坦然受之。这是两个远比女主角可爱得多的角色,属于他们的双人舞也是全剧最动人的,缠绵果决,动人心魄。
小说中,胡彩香对忆秦娥说过一段话,可以认为是对“主角”的主旨阐释——“主角,演一大本戏,其实就是看你的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都要张弛有度,不可平均受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自打你出场开始,你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势’,而是内心的自信与淡定。虽然你易青娥只有十八岁,但必须有十分成熟的心力、心性,你才可能是最好的主角。”
这一段话,可以送给每一个对《主角》再诠释的改编者。
祝后来的勇者轻巧圆润,别踩坑。
(摄影/何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