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金赫楠
焦冲小说叙事的基本场景与语境,往往都是“家”或曰“家庭”。新文学以降,“家”是一个被刻意建构的特殊场域、情境以及意象——既是物理意义上安顿和盛放个体肉身的空间,更是一个人在文化心理与情感层面上的生长原点,往往构成小说人物基本的人格和性情。“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中有多次隐喻流变,从传统道德和价值的坚固堡垒、“绝望主妇”的身心桎梏到宏大叙事中的家国同构等等。而在焦冲笔下对家庭生活与伦理关系的描摹中,人情、人性中的普遍性和幽微感得以精准显形,中国当代社会亦在“家”这个有形的特定环境中得以展现,小说也因此获得了更具代表意义的叙事说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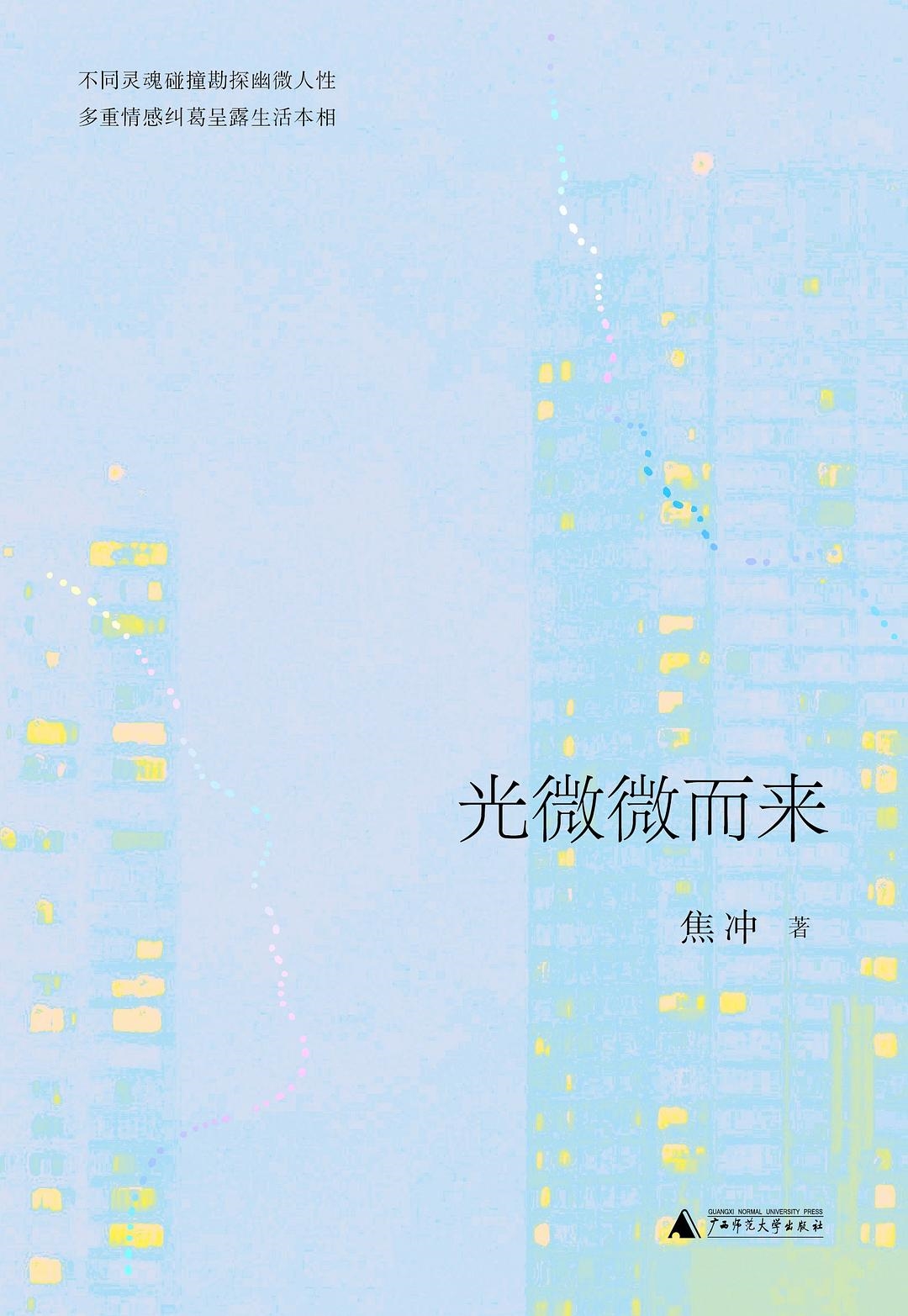
《光微微而来》,焦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
《以父之名》是焦冲前期创作的代表,作者的目光穿透人们对于家庭关系的一般想象和表层认知,展现了主人公马克与父亲之间更为复杂的相处模式与情感关系。小说开篇就设置了一种尴尬的情境:母亲突然病故而父亲不擅家务难以独自生活,马克邀父亲与自己同住,于是父子二人在马克成年之后再次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的种种矛盾不可避免地再次爆发。小说在当下讲述中还穿插了马克成长经历的回忆,让我们看到这个过程中父子之间诸多观念和情感上的错位,父子关系始终困于彼此之间的不理解、不认同,他们之间未尝没有相互的在意、关心和爱,但彼此都羞于直接表达。小说结尾处,父子并未实现和解——与对方或者说本质上是与自己的和解,尽管他们都曾以不同方式小心翼翼向前迈出过一步或者几步。在受儒学影响的东亚社会中,传统的父子关系不仅是血缘和亲情意义上的自然关系,更关乎社会权力结构和民族文化心理,因此父子冲突里往往暗含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时代镜像,《以父之名》就是以家庭生活中个体性的经验和心路历程,来反映当下一两代人都在面对和尝试解决的问题。其后,焦冲的《原生家庭》《想把月亮送给你》《梦的解析》《天灯》等小说都在围绕“家”和家庭关系展开叙事,借此更为深入地探讨家庭伦理。
焦冲擅长写女性,擅长在家庭生活和婚姻问题中塑造女性形象,表达与女性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长篇小说《女人四十》是焦冲近几年来最重要的作品。小说讲述了四位“80后”女性人近中年时的诸多际遇和起伏,处理的是作者同龄人的现实问题与成长经验。焦冲的笔墨落在主人公们的家庭生活与婚姻问题上,并由此展开对一代人的生活描摹与精神刻画。这四位“80后”女性的中年危机,其实又是每一代人必然经历的人生与心路历程。更值得一提的是,各色人物的讲述始终在一种淡然的话语氛围之下,流露出作者对自己笔下角色的深刻理解和体恤,焦冲说过,“这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慈悲”。而在2023年的另一篇小说《悬崖》中,对母女关系的探讨,再次延伸了焦冲对于亲情的多维观照和深层审视。小说描写了一个单亲家庭,母亲唐丽珊是一名过气歌手,年轻时经历过一段不伦之恋后生下女儿唐糖并独自抚养其长大。小说刻画母女关系的着力点不是两者如何相依为命,而是母亲对女儿近乎病态的生活依赖、情感捆绑甚至精神控制。文本中很多具体描写展现了唐丽珊对唐糖从生活细节到婚姻大事那种无处不在的管束和控制,读来令人感到窒息。母女二人的矛盾焦点最终落在了母亲对已经三十岁的女儿情感生活的粗暴干涉,这种干涉中固然有保护孩子的本能,但更多是一种女儿即将离开自己的恐惧,也许还带几分嫉妒——读到这里我会想起《金锁记》中曹七巧与女儿长安、《心经》中绫卿与寡母。在一次旅行中,母女二人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唐糖姿态强硬地反抗了母亲的干涉并飞蛾扑火般迅速沉溺于一场明知没有结果的情感邂逅。《悬崖》回应了现代以来诸多经典文学命题,比如历史变迁中“家庭”与个体之间动态的复杂关系,比如物理与精神意义上的“出走”等等。
阅读焦冲小说时,能明显感觉到张爱玲对他的影响,甚至他有篇小说的题目就叫作《沉香屑·第三炉香》。《悬崖》中有个片段,写到唐糖与母亲吵翻然后去赴约的心理活动:“她想起了小时候和母亲逛商场,她欣赏完琳琅满目的芭比娃娃,不见了唐丽珊,独自站在货架前,来来往往的人朝她投来陌生的目光,那一刻她孤独极了,害怕极了,仿佛被全世界遗弃。”熟悉张爱玲小说的读者读到此处,应该能联想到《倾城之恋》。这些影响一定程度上成全了焦冲的小说风格,但也会造成他后续创作思考和审美上的局限,须得提高警惕与适当地告别。
(作者系青年批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