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邓安庆
这本小说给了我非常奇妙的阅读体验,全书收录了一部中篇小说《夜雨寄北》、三部短篇《木棉或鲇鱼》《灵骨塔》《记一次春游》,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四篇作品,却都散发出那种近似于“癫狂”的气质。我相信读过的人会有同感:《夜雨寄北》里马豆芽与那只叫小丹东的猴子纠缠半生;《木棉或鲇鱼》里于慧在一个台风天想要联合前夫谋杀现任丈夫;《灵骨塔》里“我”与寺院方丈、“小三”争夺林平之的骨灰盒;《记一次春游》里“我”与以前的笔友李家玉在那一晚寻找李的丈夫……情节之离奇怪诞,让人印象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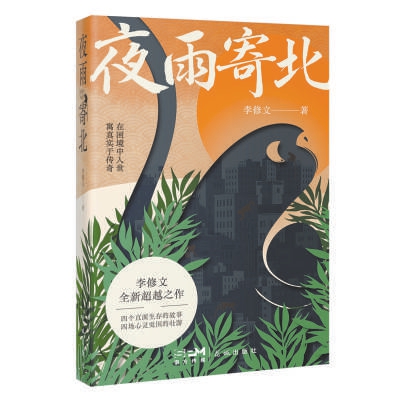
《夜雨寄北》 李修文 花城出版社
读者倘若以现实主义小说的标准来看此书,会发现其情节推动过于迅速,情节设置也不合常理,人物也多处于一种无比躁动的状态。这就像是你原本希望走在平坦的地面,从一个情节点安稳地走向另外一个情节点,但等真的进去后,却骇然地发现你被带到了跳楼机里,迅速地上升,又迅速地坠落。你忍不住会害怕,可与此同时你的肾上腺素会飙升,另外一种阅读的愉悦感油然而生。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需要换一套标准来看这些作品。
回到作品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是同名小说《夜雨寄北》。这是一部大中篇,占全书几乎一半的篇幅。马豆芽与小丹东,一个是人,一个是猴,猴通灵性,渐渐变得像人,到后面甚至干脆成了猴形的人。它在人世间沉沉浮浮,既受到了人的背叛,它也控制折磨人,人在它面前展露了兽性,它在人面前流露出了人性,可是到后面它也有了人的兽性……人性与兽性,人与兽都兼有,小说的内在复杂度也就有了,这也是我读这篇小说感觉分外有意思的地方。
另一篇《木棉或鲇鱼》,原本以为是妻子联合前夫谋杀亲夫的老套故事,看到最后才意识到原来我们已经落入了作者设置的叙事圈套里,我们以为的那些确定的信息全都要推翻,前夫原来是“鬼”,那么生动的谋杀细节居然并没有发生;《灵骨塔》里,山顶水库泄漏,洪水滔滔而下,众生相描写尤为精彩,有着非常荒诞而奇崛的想象力;《记一次春游》里,在让人眩晕的叙事狂欢中,出现了一只狐狸,而寻找的人是幽灵……可以说,全书读下来,有一种“恍惚感”,或者说失重感,那绝不是读现实小说能体会到的。
其实,一开始,作者就在自序里给了我们一把正确推开小说之门的钥匙:“蒲松龄时刻”,也就是说他希望读者以阅读《聊斋志异》的心态来对待他的作品,“志异”可以说很好地概括了这四篇小说的特质。作者在前言写道:“通过写作,我建起了这一座座衣冠冢,那些并不惊人的小事,都被我埋葬在了其中,并且越来越安顿于自己的命运:要像蒲松龄一样,在他的世界里,人也好,鬼也罢,都有一个去处。这个去处,白日里没有,就去夜晚里找,阔大城池里没有,就去荒郊野外里找。还要像蒲松龄一样,并不是妖狐鬼怪,却常常能打开一扇让我们的肉身从世界里遁形而去的门;并没有死去,却拥有一双回望尘世的眼睛。是的,我们所怀想、追忆和凭吊的,其实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作者另外一番自白,也吸引了我的注意,“也许,我要写下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热烈,他们徒劳,他们既不是世界的出走者,也不是破门而出的人,他们不过是承受了他们所在的那个世界的人。”
在这两段自我剖白中,我注意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去处”,在这四篇小说里,每一个人(猴、鬼)的确是在寻找“去处”,人生欲求安稳而不得,或主动或被动地陷入到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哪里才是安妥此生的地方?很难找到。而这个过程何其艰难曲折,其中的甘苦,被作者写了出来。另外一个是“承受”,形象地概括出了作者笔下这些人物应对命运的方式。但这些命运看起来不能自主的人,为了生活,他们使尽了全身的气力,哪怕结局没有那么圆满。
由此可见,看起来狂欢叙事的背后蕴含着作者的一颗慈悲心。作者以此观照世间万事,正如蒲松龄写鬼神狐媚,剥开后是真切的世道人心。(邓安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