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酒为骨,义为魂
——吉剧《积德泉》的家国叙事与艺术突破
作者:艾超南
大型吉剧《积德泉》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之一,也是吉林省首部吉商题材大型原创吉剧。全剧以清末至伪满时期为时间轴,围绕“齐家烧锅”(后更名为“积德泉”)女掌柜“齐家二奶奶”张桂芝跨越三十年的经营历程展开,在六幕跌宕起伏的剧情中,将吉商精神与家国大义熔铸为一曲荡气回肠的时代悲歌。该剧既延续了吉剧贴近生活、诙谐质朴的艺术基因,又突破了传统地方戏的叙事边界,以创新的舞台语言、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深刻的精神内核,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美学感染力的关东文化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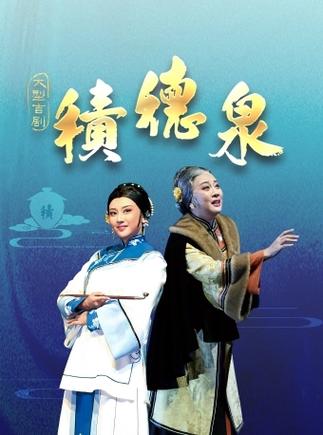
舞美设计:藏露之间的东方意蕴
《积德泉》的舞美设计在“用视觉讲好故事”这一点上表现优秀。从序幕到终场,很多细节都蕴含着东方美学的情韵与剧情伏笔。序幕中“红色小腿舞”(笔者取名)的呈现,一开场就带给人视觉与情感上的双重冲击——悬挂的屏风遮蔽舞者上身,仅让一排着红色长裤的小腿在光影中翩跹,这种设计主动舍弃了肢体的完整呈现,却通过局部动态的聚焦,使舞蹈的节奏感与力量感更具冲击力,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藏与露”的辩证思维,如同传统水墨画中的“留白”,为台下观众留下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
剧中道具与色彩的运用则形成鲜明的符号体系。比如第一场“烧锅易名”中的酒坛舞——大大的黑色酒坛上贴着红底黑色“酒”字贴纸,在视觉上构成强烈对比,既凸显了关东酒文化的厚重底色,又让人联想到“红火日子”与“时代阴霾”的矛盾冲突;青年壮汉手举酒坛,以刚劲的肢体语言,将吉商“以酒兴业”的创业激情具象化,再配上激昂的大鼓声和铿锵的铙钹声,形成充满生命力的视听双重景观。而第三场“无奈嫁女”中,日寇的淫威致使酒坊内忧外患、难以为继,桂芝的女儿齐少筠被迫即将嫁给孙掌柜家病入膏肓的孙子。此时,十数条长长的白练突然从舞台顶端唰地一下垂落,并随着剧情和少筠的唱词逐渐转为红色,更是将戏剧冲突推向高潮。白色既象征着少女的纯真,又像“丧事”,隐喻着梦想的破灭与命运的悲凉;红色本是喜庆的颜色,但在剧中,却主要隐喻着巨大的牺牲。两种颜色的渐变过程,恰似少筠从“红妆待嫁”到“为家分忧”的心理蜕变,优秀的舞美设计能帮助观众轻松读懂剧中人物的隐忍与担当,从而与剧中人同悲欢、共命运。
人物塑造:立体丰满的吉商群像
《积德泉》的核心魅力,在于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立体丰满”的吉商形象,如张桂芝和她的儿子齐少武、女儿齐少筠、大侄子齐少文,以及复杂的“反派”、怀揣一流鉴酒本领的关得利等。其中女主角桂芝的刻画尤为立体。作为齐家烧锅的掌舵人,她既是“寡妇掌柜”,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侄子的二娘,多重身份让她的抉择始终在“小家”与“大家”之间拉扯。第一场“烧锅易名”中,长期受到齐家恩惠的父老乡亲集体送了桂芝一副对联:水好酒好人品好,积德积善积财源。桂芝于是将“齐家烧锅”改名“积德泉”,这一情节不仅点明“以德兴业”的吉商精神内核,更展现了她超越个人利益的格局——在她眼中,烧锅早已不是齐家的私产,而是承载乡亲信任、维系一方生计的“共同体”。
面对困境时,桂芝的“柔”与“刚”形成鲜明反差。第二场“少武离家”,她对儿子齐少武唱“谨言慎行保安宁……关东儿女铁骨铮铮”,既是母亲对孩子的牵挂,也是关东人面对强权时的骨气;第五场“刑场别子”堪称全剧最催泪的段落,母子在刑场上不能相认。少武为了不连累母亲和齐家,至死也没有喊一句“娘”,而是称呼她为“这位老人家”。桂芝也没有认下自己的亲儿子,俩人只能通过“如果我有一个你这样的儿子,来世我还要做他的亲娘”“如果我有一个您这样的亲娘,来世我还要做他的儿子”的唱词来传递思念。桂芝强忍悲痛的眼神、颤抖的双手和佝偻的背,将“母亲”的柔情与“中国人”的尊严与刚毅融为一体——她知道儿子必死无疑,而一旦相认,不仅儿子性命难保,父老乡亲都会被牵连。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抉择,让“积德”二字从商业信条升华为民族气节。除桂芝外,其他人物的刻画同样避免了脸谱化。少武从懵懂少年成长为东北抗联战士,他的离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受母亲“忠善仁义”教诲的必然结果;少筠被迫嫁入孙家,从“灯阑珊愁云低锁映孤窗”的哀怨,到“娘亲柔肩挑重担,少筠红妆守家园”的觉醒,展现了关东女性“外柔内刚”的特质;即便是反派关得利,也并非单纯的“坏人”,他的贪婪与背叛背后,暗含着动荡时代中人性的迷失,最后他在大是大非面前也展现了一种“虽迟但到”的悔悟。这种复杂的人物设定,让剧情更具真实感与说服力。
剧情冲突:家国危亡中的道义坚守
《积德泉》的剧情架构以“冲突”为驱动,将家族沉浮与民族大义两条线索紧密交织,形成层层递进的叙事张力。从第一场 “烧锅易名”确立“以德兴业”的基调,到第二场“少武离家”引入日本人觊觎秘方的外部危机,再到第三场“无奈嫁女”的家族内部矛盾爆发,剧情节奏张弛有度,每一场冲突都推动了人物的成长与主题的深化。
剧中最具张力的冲突,在于“经商”与“道义”的抉择。当日本侵略者查封积德泉、诱迫少文签订合约时,桂芝面临的不仅是“要不要为日寇提供军需酒”的商业问题,更是“要不要做亡国奴”的民族问题。张桂芝的选择给出了答案:她拒绝交出所谓的“秘方”,甚至在日本人发动细菌战时,将积德泉变为救助百姓的“福地”。剧中通过管家之口表达百姓称赞“积德泉是福地”时,张桂芝却反问管家“福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才是福地……”,言外之意不言自明:现在家国被侵略,哪里是福地?这种矛盾冲突直击人心,既道出了关东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也揭露了侵略战争的残酷本质。而第六场“玉石俱焚”的结局,更是将剧情推向高潮。桂芝送走少文和孙子等一大家子,诀别前夕,桂芝郑重地取出一个精致的匣子,终于将酿酒“秘方”——一张写着“积德”二字的纸条传给了少文。而她自己选择独自留下来,火烧酒坊,与日寇同归于尽。这一选择并非冲动之举,而是她对“积德”精神的终极坚守:酒坊可以烧毁,但“积德”的信念不能失传;生命可以牺牲,但民族的尊严不能被践踏。当火焰吞噬酒坊时,伴随着男声高亢悲怆的唱词:“一眼神泉润万疆,一生正道是沧桑,一锅老酒正气长,一脉相传兴家邦”,不仅是对桂芝一生的总结,更是对吉商精神、民族精神的传承,让全剧的主题从“家族兴衰”升华为“家国存续”的宏大叙事。
整体而言,作为一部地方戏,《积德泉》不仅在艺术表达上有创新,而且吉商题材的厚重感也突破了传统地方戏多以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为题材的局限,拓展了吉剧的叙事边界与思想深度。剧中人的故事早已落幕,但“积德”二字所蕴含的诚信、道义与担当,却永不过时。在当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积德泉》的创作与传播,不仅为吉剧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更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份精神滋养——正如那锅传承百年的老酒,唯有以“德”为曲,以“义”为粮,才能酿造出跨越时空的醇香,才能让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作者系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