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唐 山
提起抗战史中的“文化抗战”,人们会立刻想到故宫文物南迁、西南联大奇迹、“孤岛”文学、保护毛公鼎等例子,却鲜有人注意到,在1937年至1945年间,上海还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文化暗战——保护古书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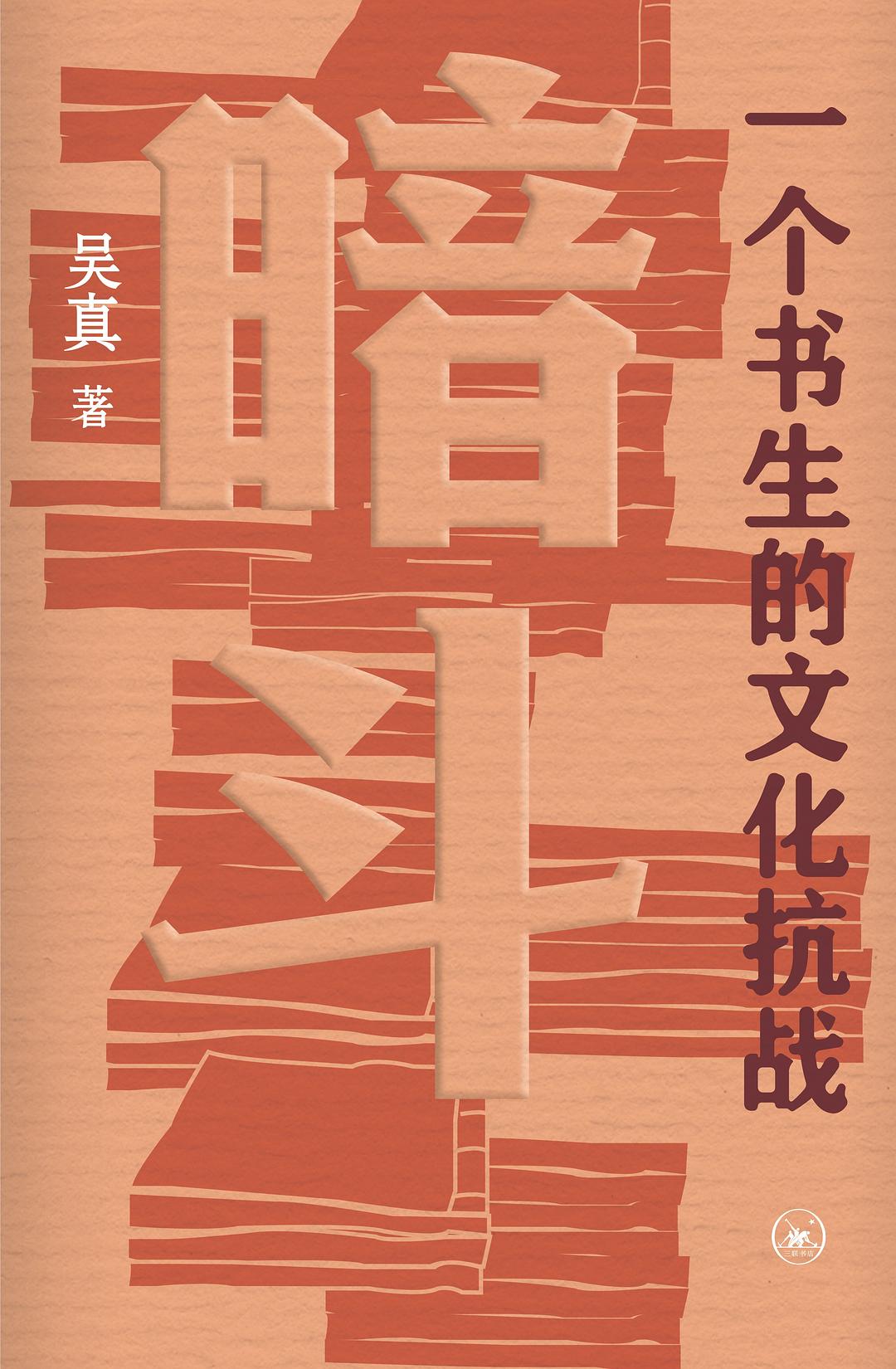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封面
此战难度巨大:除了日军掠夺古书外,美国、英国等“友邦”也进行了公开掠夺;1939年底,国民政府表态,无经费支持;许多中国书商助纣为虐,“平贾”(来自北平的书商)纷纷南下,甘当日本书店、美国大学的傀儡;而在日军与日本文化特务的监视下,保护工作只能在暗中进行……
然而,在郑振铎的牵头下,张元济、何炳松、张寿镛等人秘密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累计收购善本4.8万册,并在“珍珠港事变”前,在唐弢、许地山等人的帮助下,奇迹般地将近三千种古籍精品运输至香港。在抗战的最后4年里,郑振铎隐姓埋名,每天只吃一顿饭,卖尽私藏,仅能维持全家最低标准生活……在这本《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三联书店,2025年7月)中,作者吴真钩沉出这场不为人知的文化抗战的细节,描绘了旧书业风貌,更重要的是,呈现了老一代读书人的操守、智慧、奉献与忠诚,他们的功业与山河日月永存。
日军抢古书,意在文化灭绝
侵华战争的根本目的,是用军事侵略、资源掠夺和文化灭绝等方式,实现对中国领土的永久占领,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其中“文化灭绝”是其中的重要手段。
名书商陈乃乾撰文称:“道路传言,谓各地私家所藏图书金石书画骨董,悉为军队囊括而去。斯言也,我未之能信。盖军队进退仓卒,未能有此闲暇,即闲暇矣,未必能鉴别以定取舍也。”陈乃乾此说误甚。日军对江南文献的掠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1937年12月,上海派遣军特务部设“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每占一地,即特派图书管理员,与“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南满铁上海事务所”等合作,专抢文化资料。
战前我国共3744家图书馆,1937年底已失2166所,损失图书近9000万册,还不包括民间藏书的损失,堪称人类书籍史上罕有的浩劫。作家阿英在1938年的《如此烧抄》一文中记:“字画书籍,(侵华日军)随队皆有鉴别人,书画割去四周,以便携带。全部抄完,然后就烧。”作家徐迟在《南浔浩劫实写》中,记1937年11月19日,日军在南浔古镇进行的图书抢劫:“宋、元、明版珍藏书集,一箱箱的扛出来……我怀疑‘他们’所以从平望进展到南浔如此之迅疾,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把藏书先行占领,是可以显见其用心之深的。”
据张怿伯在《镇江沦陷记》记:“敌兵在镇江,劫得许多古董玩器,装箱运走,嘱由某理发店,代开一假发票,并盖店戳,闻系为避免海关盘诘……明明系抢劫得来,但要蒙混得过人,即可作为买进来的,所谓‘皇军’,于这些鬼祟之事,做得如此之工,真是无所不能。”
为搜刮殆尽,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梅”机关(特务机构)负责人之一清水董三亲到上海中国书店找郑振铎,日本学者高仓正三被派驻苏州,多次约见郑振铎,约不到,于是就在郑常去的书店枯等。
为抹去中国人的文化记忆,日方可谓费尽心机。
为一套书,受尽了冤枉
郑振铎参与暗战,既偶然又必然。先说偶然因素:
郑振铎本是书痴,多藏被时人鄙夷的古唱本。1932年“一·二八”事变,郑家被日军占领,所藏2万余册唱本皆失;后重新收集,又得1万多册,毁于1937年淞沪会战;郑振铎带在身边的400多册珍品才得以幸免。
两次“精准打击”,可能表明日军早知郑振铎在曲籍收藏上是“海内私家之冠”。郑曾印《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40本,非卖品,仅赠与好友和大图书馆,日本竟收藏了8本。
江南沦陷后,大量古书流落上海。1938年,郑振铎遇稀世珍品——64册《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简称《古今杂剧》),是明代礼部尚书之子赵琦美利用在北京任太常寺典簿11年之机,将宫廷内府剧本抄出,其中收录的多为久未传世的珍本。
该丛书被两家掌控,预估3000元,郑振铎初托陈乃乾收购,考虑到陈乃乾与其中一家有积怨,又托当时上海最大的旧书店“来青阁”的店主杨寿祺去谈。陈乃乾是所谓“包袱斋”,没店面,两边说合,得10—20%的佣金。可能陈乃乾对郑另找别家不满,又劝说古董商孙伯渊速将全书收入手中,叫价到1万元。价格蹿升如此惊人,引陈乃乾等抓住郑振铎急于得到的心态,但郑买不起,便与南迁的北平图书馆等联系,希望收购,遭拒。恰在此时,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知此事,从教育经费中拨款购书。
老友叶圣陶对此不满:“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
多年后,郑振铎撰文称:“我为此事费尽了心力,受尽了气,担尽了心事,也受尽了冤枉……这是我为国家购致古书的开始。”
偶然中也有必然因素。上海沦陷前,郑振铎面临“走或留”的抉择,可他的孩子刚出生,全家10口人,逃难风险大。可留下后,郑振铎又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为国家收书,以免“史在他邦,文归海外”,这是郑振铎找到的新的人生方向。
节外生枝,古书差点全军覆没
收《古今杂剧》后,郑振铎试图保护更多古书,1939年12月底,重庆来电,表示政府无钱投入,鼓励“文献保存同志会”自募资金,为国家搜访文献,胜利之后,再连本带利偿还。
郑振铎并未退缩,他表示:“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殂代谋者。”1940年1月4日,事突有转机,中英退还庚款董事会的董事叶恭绰,在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的堂侄)的游说下,同意每年拨购书款,三分之二给上海,三分之一给香港。
1940年起,“平贾”纷纷南下,“几乎每一家北平书肆都有人南下收书,在那个时候,他们有纵横如意、垄断南方书市之慨”,而古书中“寄平的,十之八九不能追得回来”,这一部分多落到日本人手中。这一年春夏,江南各大藏书楼均放风出售藏品,“此数月中城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关头也”,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趁火打劫,疯狂采购。同年9月时,郑振铎抱怨道:“近来书价之高,可谓骇人听闻!”
好在“文献保存同志会”的资金充足,1942年时,“文献保存同志会”除了得到中英退还庚款董事会的120多万元外,还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追加的拨款200多万元。
当时“平贾”中的“三王”(王富晋、王晋卿、王子霖)中的前两位,还有孙殿起、陈济船、孙实君、孙助廉等高手,均驻扎在上海,成“围攻”之势。郑振铎一面以民族情感说服竞争者,另一面出价高,使“我所拣剩下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
郑振铎预判日军即将占领租界,托时任上海邮局甲等邮务员的唐弢(后成著名文学评论家)先后向香港寄出3000多个包裹,这3000多种珍品书从日军严厉监管的鼻子下,到了香港,经许地山先生安排,暂藏在冯平山图书馆。
日军攻占香港前,叶恭绰准备将这批书送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陈立夫却节外生枝,称书到国外前,应全部加盖“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印。已打包好的书紧急拆箱盖章,忙了3个月,错过船期,被日军全部掳走。
抗战后追索被劫文物,在日本找到了这些古书,才将它们收回。
一介书生,却成了战胜者
日军攻占上海租界后,“文献保存同志会”其他成员撤离,郑振铎留下保护未寄香港的3万多册古书。郑振铎给好友留下遗嘱。因上了“梅机关”的14人黑名单,不愿拖累家人的郑振铎在抗战的最后4年离家独居,只因祖母去世匆匆回家过一次。
1942年1月,日军在上海实行配给制,没市民证买不到米、油、煤等,郑振铎通过一家文具店办了职员证,天天闲逛,以示上班。1943年1月,郑振铎路遇樊仲云,二人曾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同事,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成立最早的新文化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樊仲云又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据1943年11月重庆《中外春秋》报道:“一天晚上,樊逆在棋盘街转弯的弄堂口,遇见郑正在出神地翻阅旧书,樊连连拍其脊背,郑仍不理,樊又拍了几下,郑才微转其首,刮目相看,知是樊逆仲云,不作一声,立即拔步狂奔,樊逆亦不与语,只是跟踪追赶……郑氏终于逸去,樊逆大呼懊丧不止。”
为了保密,郑振铎在文章中隐去大量信息,旧书行中,卖家是多年好友,联系买家也会请中间人操作,许多重大交易完成后,卖家多年不知买家是谁。郑振铎买了什么、如何操作,连他最好的朋友都不清楚,致这一段紧张激烈的“古书抗战”长期不为外人所知。
郑振铎曾撰文:“在最近二三年的动荡不安的生活里,最足以看出‘士’能不能‘安’‘贫’的品格来。”“这世界集合这一群不能‘安贫’的‘士’在翻天覆地的混扰着,还不成了禽兽世界么?”
在沦陷区,郑振铎不写稿、不任职、不参加社会活动,1943年,20余岁的张爱玲在文坛名声鹊起,他和柯灵建议别急着成名,张爱玲回以她自己对时代的态度,于是就有了那句名言:“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取”与“去就”,考验着每一代读书人。读《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不只为了解一个时代、看懂一个人、聆听几段故事,更为自问:我该如何楔入时代?我该如何填好自己的答卷?(唐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