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土山石
谈论舞美的好坏,而非规模的大小
——一名舞美从业者对“舞美大制作”批判潮的四点反问
近来,戏剧圈弥漫着一股奇特的“道德审判”,审判的中心,恰恰是我们这些终日与图纸、模型、光影打交道的舞美从业者。
一篇篇檄文,一场场论坛,似乎一夜之间,“舞美大制作”就成了戏剧艺术的万恶之源,成了艺术本体迷失、创演生态异化、资源极度浪费的罪魁祸首。有将舞美大制作比喻为“翅膀绑上黄金”的,有把舞美大制作定义为“异化生态”的,还有人义正词严地说“舞美庞杂挤占表演空间”的。我读这些文章,起初是自省,继而是困惑,最终是压抑不住的愤怒。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善意的、基于理解的专业探讨,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充满了知识壁垒的傲慢,和对舞台美术这门专业彻头彻尾的无知。
他们似乎已经完成了审判,只等着将我们钉上名为“返璞归真”的十字架。但在行刑之前,请允许我,代表那些在黑暗中追逐光影、在方寸间构建世界的同行们,发出我们的声音,提出我们的四点反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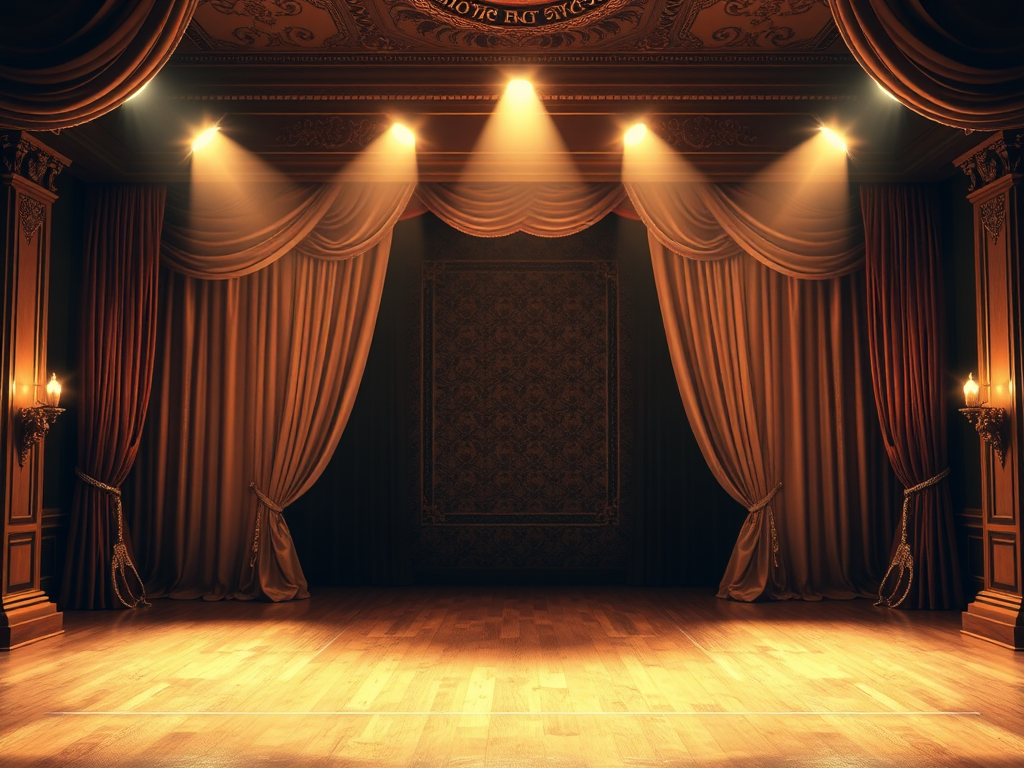
第一问:何为“大”?谁在定义“大”?
在所有批判的开始,都有一个模糊不清、却被用作万能武器的前提——“舞美‘大’制作”。但请问各位批评家,当我们谈论“大”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 是制作费用的数字吗?十万元的舞美制作费用算大吗?对于一个县级剧团来说,那是天文数字;但对于一部志在夺奖、巡演的大型剧目来说,可能只是九牛一毛。
● 是布景道具的体量吗?拉了几卡车的道具就算大吗?某外国舞美设计师受邀来设计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装台的时候拉了近百车的布景道具。脱离戏剧题材去谈论布景体量,本身就是偷换概念。
● 或是那些被运用到舞台上的新技术?用了转台、升降、LED、全息投影就算大吗?如果要演绎的是一个关于未来、关于数字世界的剧本,不用这些技术去构筑它的虚拟与宏大,难道要退回到用“一桌二椅”去比划吗?
批评家们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将“大制作”这个词标签化、污名化,用一个极其业余的、充满主观偏见的标准,去衡量一个高度工业化和艺术化的专业领域。在他们眼中:
●《狮子王》那种将非洲草原的生命律动搬上舞台的史诗级创造,是“大制作”;
●《Sleep No More》那种用整栋楼宇构建一个让观众迷失的麦克白梦境,是“大制作”;
●《只此青绿》那样用巧妙的舞台机械和光影再现《千里江山图》的东方诗意,也是“大制作”。
然而,这些剧目之所以伟大,恰恰在于它们的视觉构想之“大”,是艺术追求之大,是想象疆域之大,是技术与艺术完美融合后所能达到的表现力之大。它们的舞美,不是剧本和表演的“外包装”,而是与之一同呼吸、共生共荣的血肉筋骨。砍掉它们的舞美,不是“返璞归真”,而是直接毁掉了作品本身。
所以,在戏剧的世界里,舞美没有绝对的“大小”之分,只有“好坏”“巧拙”“适配与否”之别。一个耗资百万但精准服务于剧情、开拓了审美边界的设计,是“好”的;一个仅花一万但与全剧格格不入、暴露了主创审美贫瘠的设计,是“坏”的。
用外行的、模糊的“大小”概念,来替代内行的、精准的“好坏”评判,这是典型的、源于知识壁垒的傲慢。
第二问:舞台的艺术追求,何以沦为舞美的原罪?
好,即便我们退一步,承认存在那些“失败的大制作”,即预算超标、效果拙劣、喧宾夺主的案例存在,那么,下一个问题是:这份罪责,应该完全由舞美设计师来背负吗?
批评家们似乎默认了一个前提:舞台上的一切视觉呈现,都源自舞美设计师个人的主观意图和审美偏好。这暴露了他们对戏剧创作流程的惊人无知。
在一部戏剧的创作链条中,舞美设计师是拥有最终决定权的人吗?从来不是!
一个项目的立项,往往来自剧院团的年度规划、地方政府的文化任务和资金扶持,或是制作人的商业考量。从立项之初,这部剧的体量、定位和预算的天花板,就已经被框定了。这是“资方”的意志。
随后,导演作为全剧的艺术总负责人,会提出他的创作构想。剧本给了他一个世界观,他需要决定这个世界观是以写意还是写实、以简约还是繁复的方式呈现。他会说“我需要一个天崩地裂的效果”“我希望舞台能像电影大片一样自由切换”“我想要一个让观众惊掉下巴的开场”等等(当然还有因为导演的亲朋好友是做视频或设备租赁的,而要求使用某种效果的,这不在艺术追求的讨论范围)。这是“导演”的意志。
而荒谬的现实是,对于绝大多数在基层院团工作的舞美设计同行而言,他们面临的困境无比尴尬:既怕院团资金不够,自己的构想无法实现;又怕院团资金“过于”充足,因为充足通常意味着院团会外请“大咖”来设计,自己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有的大咖,仅仅设计费,就比肩甚至超过了普通舞美设计师全年所有戏的制作总费用。当批评家们将矛头对准“舞美大制作”时,他们可能不知道,绝大多数本土的、基层的舞美设计师,连“大制作”的门槛都摸不到,又何谈去推动和主导它呢?
所以,我们这些舞美设计师,是在这个巨大的框架之下,戴着镣铐跳舞的人。我们的工作,不是天马行空地想“我想做什么”,而是在给定的预算内,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技术储备和艺术想象力,去实现导演的艺术构想,去满足剧本的叙事需求。我们是“实现者”,是“翻译官”,是将文本和导演的脑内风暴,转化为可见、可感的舞台空间的工程师和艺术家。
当一个项目因为“好大喜功”的初衷而立项,当一个导演缺乏把控力、只想用视觉奇观来掩盖叙事的苍白,当一部剧本本身就空洞无物、只能靠“大场面”来填充时,最终呈现的舞美,必然是臃肿、昂贵且空洞的。
舞台的艺术追求,本应由全体主创共同承担,如今却被异化为舞美的原罪。对舞美大制作的这份指摘,怎么就精准地落到了舞台美术行业的头上呢?这相当于将系统性的决策问题,简化为某个部门的“主观故意”,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寻找替罪羊的行为。这种责任的错位与转嫁,暴露出的,是对行业运作逻辑的无知。
第三问:砍掉“大制作”,戏剧就会“返璞归真”吗?
许多批评文章的最终落点,都是呼吁“回归戏剧本体”“回归一桌二椅的东方美学”。这个口号听起来无比正确,充满情怀。但我想问,在今天,这种“回归”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审美上的自我设限与作茧自缚。
戏剧,从来不是活在真空里的艺术。它与时代同呼吸,与科技共命运。当电影工业已经用IMAX和虚拟现实技术将观众的感官体验推向极致,当短视频用碎片化的强烈刺激占据着人们的闲暇时间,戏剧,这门古老的艺术,靠什么去争夺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注意力?难道就靠告诉他们“我们这里很朴素,请尽情想象”吗?可是在今天,对于大多数习惯了视觉轰炸的观众而言,这不是一种吸引,而是一种劝退。
我们当然要坚守戏剧的内核——故事与表演。但这与我们拥抱前沿的舞台技术、探索更丰富的视觉表达,从不矛盾。“一桌二椅”的假定性,在那个物质匮乏、娱乐单一的年代,它是智慧的结晶,是美学的巅峰。但在今天,如果我们还把“一桌二椅”奉为所有戏剧都应遵守的唯一圭臬,那不是传承,那是思想上的懒惰和文化上的不自信。
砍掉“大制作”,戏剧不会变得更好,只会变得更“穷”,更“小”,更“边缘”。
● 表现力的“穷”:我们将失去处理史诗、神话、科幻等宏大题材的能力。我们将无法创造出让观众沉浸其中的幻境。戏剧的题材和表现手法,将被人为地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
● 观众群体的“小”:我们将主动放弃与电影、游戏等其他视觉艺术争夺观众的权利,蜷缩回一个小众的、同温层的艺术圈子里自娱自乐。这对于戏剧的普及和发展,是致命的。
● 行业发展的“边缘”:由此一来,舞台技术、设备制造、专业人才培养等一整条产业链的创新和发展都将停滞。我们将眼睁睁看着百老汇、伦敦西区的同行们用最新的科技创造着舞台奇迹,而我们自己,却抱着“陈规旧习”故步自封。

电脑灯技术 。(图片源于网络)
批评家们对“技术”的警惕,近乎于一种本能的怀疑。他们似乎认为,技术是艺术的敌人。然而,从古希腊的“机械降神”,到莎士比亚时代的吊杆、地板门,再到今天的电脑灯、伺服电机、增强现实(AR),这些都说明,技术,永远是拓展舞台艺术边界最得力的助手。
但是问题从来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使用技术人的“审美”。用“返璞归真”的情怀,来行审美倒退之实,这是对戏剧未来的不负责任。
第四问:系统性浪费面前,舞美成为了替罪羊?
这是我最想问,也是我最感到荒谬的一点。几乎所有批评文章都痛心疾首于舞台大制作导致“资源浪费”,并将矛头精准地对准了舞美行业。这仿佛一栋建筑因各种原因最终烂尾,所有人都不是去追究最初的决策者、投资方和负责保障的监管者,而是将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出图纸的“绘图员”(设计师),并指着图纸说:“就是你们的设计图纸太复杂、用的材料太贵,才导致了我们这个项目的失败和烂尾!”
这何其可笑,又何其不公!
一部戏剧的诞生,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如果真的要清算“浪费”,那么,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布景道具,恐怕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之下,是更多、更惊人的、被批评家们选择性无视的浪费:
● 剧本的浪费:如果剧本结构松散、人物扁平、逻辑不通,需要开多少次专家论证会?需要编剧反复修改多少稿?需要全体主创和演员在排练场上耗费多少时间去“弥补”和“找补”?这些人力成本、时间成本、资金成本难道不是巨大的浪费吗?一个从根上就烂掉的剧本,哪怕用最省钱的舞美,它依然是对所有参与者生命的巨大浪费。
● 导演的浪费:一个在排练前毫无构想、在排练中朝令夕改的导演,是剧组最大的灾难。今天觉得这个调度好,明天全盘推翻;今天觉得布景应该在左边,临近合成时又说要改到右边,并在景片上开个门。导演每一次的犹豫和摇摆,都导致了演员的无效劳动、技术部门的重复作业,以及制作预算的节节攀升。这种看不见的“决策的浪费”,其成本远超几车布景。
● 表演的浪费:演员们数月的排练,最终因为导演调度失当、音乐喧宾夺主、舞美挤压空间,而无法淋漓尽致地发挥。他们宝贵的艺术生命,被消耗在一部平庸之作里,这难道不是最令人痛心的浪费?
● 评论的浪费与健忘:说到浪费,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批评的浪费”。因为今天许多对“舞美大制作”口诛笔伐的评论文章,其作者,正是昨天将这些作品捧上神坛的吹鼓手。
我们不禁要问:那些曾被你们盛赞为“视觉盛宴”“史诗级呈现”“开拓戏剧新纪元”的剧目,为何在一夜之间,就成了你们口中“浮夸空洞”“挤占表演空间”的靶子?是舞台本身变了,还是评论的风向变了?当评论家们放弃了对戏剧文本、对导演手法、对表演层次的“一贯性”“专业性”解读,而是随波逐流,用今天的立场轻易地否定昨天的自己,这本身就是对公共话语空间最大的浪费。
如果舞美真的有“大制作”的原罪需要反思,那么请各位评论家先进行自我反思:是什么让你们的标准如此摇摆?在声讨舞美之前,是否应该先为自己昨日的“捧杀”道个歉?
最后,说说为什么受伤的单单是舞美。
答案很简单:因为舞美是“显性”的。布景道具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花了多少钱,拉了几车货,一目了然。而剧本的空洞、导演的无能、决策者的失误,是“隐性”的,是无法简单量化的。
矛头总指向最显眼却最无言的角落。批评家们不敢或不愿去挑战一部剧真正的权力核心——出品方和导演,不敢去啃“剧本烂”这块最硬的骨头,于是,便将所有的炮火,都倾泻到最直观、也最缺乏话语权的舞美部门身上。
这,就是最根本的傲慢。一种“唯文本论”“唯表演论”的傲慢。在他们的话语体系里,编剧、导演、演员从事的是高尚的、关乎灵魂的“本体”艺术;而我们舞美,只是依附于他们的、花钱的、搞装修的“技术工人”。
所以,戏不够,景来凑;戏不成,景背锅。
结语:让我们谈论“好坏”而非“大小”
我无意为那些粗制滥造、华而不实的舞美设计辩护。行业内确实存在问题,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反思和努力。但我坚决反对当前这种简单粗暴、转嫁矛盾、污名化舞美专业的批评浪潮。
请各位批评家在下笔之前,先放下身段,去了解一下戏剧的创作流程,去尊重一下舞台美术的专业性。一部戏的成功或失败,是全体主创的成功或失败。舞美,不应是戏剧失败的“遮羞布”,更不该成为平庸作品的“替罪羊”。请不要再用“大制作”这样模糊的标签,来替代对一部剧艺术质量的综合评判。
让我们把讨论拉回到真正的专业轨道上吧。让我们去谈论,一个舞美设计,是否精准地传达了戏剧的精神内核?是否为表演创造了富有表现力的空间?是否与导演的阐述同频共振?是否给观众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让我们谈论“好”与“坏”,而不是“大”与“小”。否则,今天你们以“返璞归真”的名义砍掉了舞美,明天,当你们发现戏剧依然平庸时,又准备将谁推上那个被献祭的十字架呢?
最后,我想起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明明喝水就能解渴,为什么人们还要去喝茶呢?因为水的功能是“解渴”,而茶的价值在于“品味”。茶叶的制造成本和售价远高于水,连泡茶的过程都被称为茶艺,相对水来说,茶算不算一种“大制作”?当然算。但我们品尝它,是为了体验其背后的风土人情、复杂工艺、独特文化和社交氛围——这些是白开水无法给予的、更高维度的审美与精神享受。
戏剧同理。有的戏要求舞美如水,纯粹质朴,满足戏剧最基本的叙事功能。有的戏要求舞美如茶,层次丰富,能调动人的五感,营造一个令人沉醉的世界。
我们既需要水来解渴,也不能放弃品味好茶的权利。
请不要用“解渴”的功利主义,来审判一杯好茶的价值。
戏剧,值得回味悠长。(土山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