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周郎顾曲
汪曾祺从民国时期就开始写散文和小说。上海三联书店曾出过一本《前十年集》,收录了他前十年发表的作品。但在四十年代,他的名气并不高,只能算一位风格独特的青年作家,作品传播局限在文人圈内。
有趣的是,改革开放后,汪曾祺迎来作品的井喷期。1979年到1981年,他的小说《骑兵列传》《受戒》《异秉》和《大淖记事》先后发表,不仅引起严肃文学圈子的热议,也在民间掀起了“汪曾祺热”。这股热潮开端于八十年代,火热于九十年代,蔓延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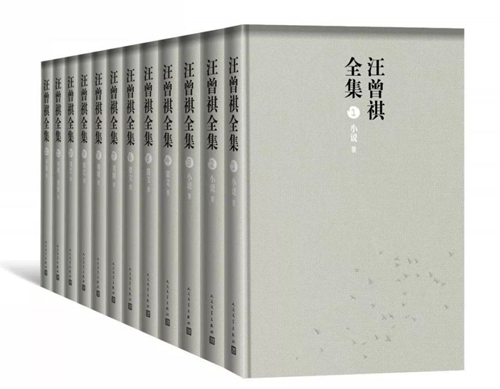
汪曾祺为什么在晚年走红?他的文学特别在哪里?这需要追溯到改革开放前国内的文学环境。改革开放前,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泛滥,“宏大叙事”“英雄史诗”支配了文学创作,注重审美和个人情感的文学被压制。当时,汪曾祺的文学主张与主流格格不入,那些清新缱绻的文字,被当作了小资产阶级美学趣味的靶子。
其实,汪曾祺对平民有更多关切,他的作品中流露出的“抒情”与“边地特色”,让中国文学悄悄流淌出一条清流。可惜在“文革”时期,这样的文学并不被提倡,汪曾祺只能选择后退,等待时机。直到改革开放,他的文学才有了施展的良机。
七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宏大叙事支配文学太久,使得“地下”文学引起了更多青年人的兴趣。北岛、芒克、多多等人,象征了诗歌美学复兴的晨光。而在小说、散文界,读者也迫切希望看到不同于“革命+恋爱”模式的文字,能重新给予他们精神和审美上的愉悦。汪曾祺重出江湖,恰在其时。
尽管在七十年代末,对汪曾祺的讨论仍然局限在文学圈内,但在当时,一些评论家已经意识到他的特别。曹文轩后来回忆道:“有见识的读者和评论者,都有一种惊奇,觉得总在作深沉、痛苦状的文坛忽地有了一股清新而柔和的风气。”王德威敏锐地发现了汪曾祺的文学脉络——他的作品不但深受沈从文的影响,而且与叶绍钧、周作人、废名、何其芳、卞之琳等人都有着微妙的牵连。
汪曾祺在文学中构建了一个消解史诗、消解暴力的诗意乌托邦,创造了一个“去政治”的文学世界。汪曾祺的文学是清新的,他排斥暴力,不愿在散文中书写沉重或血腥的场景,即便是涉足武侠小说,也会使用诗化的语言将读者的目光集中在地域风情、人物情感等方面。在轻盈的美学世界里,汪曾祺写意地描绘了一副风俗画。他的作品常常有一个套路,那便是先引出“这个地方”,然后呈现一大段工笔似的风土描写,就像一位画师,在白纸上徐徐勾勒出鲜明的意象。在这些风俗画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抹洁净的色彩,哪怕笔下是泥淖,经由汪曾祺的处理,仍有干净之气。这般干净气息,服务于汪曾祺构筑的童话世界。
汪曾祺写的童话故事含有以坦诚、纯真为核心价值的道德体系。这是一个刻意与世故世界对立的纯真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放大了童年的善良与美好,像电影剪辑一样,剪去了琐碎无聊、暴戾烦闷的部分,赋予文本梦幻感。在这个乌托邦里,人与人交往贵在真诚、义气,一个平凡的乡野人家,也可重然诺、轻生死。而男男女女的情愫,真真切切如同初恋一般,“禁欲”却美好。所以《岁寒三友》中,清贫画师靳彝甫,交友只看“义气”二字;《皮凤三楦房子》中,皮凤三也是个仗义疏财,打抱不平的主儿。
继承了恩师沈从文的故事趣味,汪曾祺喜欢书写边缘土地的故事,这个地方往往是城市人已不熟悉的遥远乡村。而乡村里的人,他们的处世观念与道德气息,也和市场化浪潮中的都市截然不同,那些古老的村社图景,勾引起读者对淳朴生活的怀念。汪曾祺能够持续走红,某种程度上也因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城乡剧变的关键时期,大量传统乡村和民俗消亡,青年们却还不能完全适应城市生活的紊乱与孤独。而汪曾祺的作品就像逆水行舟,指引他们回到退避现实的田园牧歌。
汪曾祺的创作实践得到了许多年轻作者的响应,九十年代后,文学创作进一步加速对政治与道德的切割,拒绝宏大、诉诸日常的文学作品成为年轻作者的选择。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文学还体现出浓厚的政治关怀,那么在九十年代后,以新写实主义、乡土写作、日常书写等名目编织的文学写作图景,表现出作者们极力从政治与道德议题中抽身,关注自身欲求和审美趣味的写作倾向。轻盈的文学流行,严肃的议题被压制,文学作品愈发成为远离现实政治的湖边小屋。(周郎顾曲)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面向社会长期征集优秀稿件。诚邀您围绕文艺作品、事件、现象等,发表有态度、有温度、有深度的评论意见。文章2000字以内为宜,表意清晰,形成完整内容。来稿一经采用,将支付相应稿酬。请留下联系方式。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投稿邮箱:wenyi@gmw.cn。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面向社会长期征集优秀稿件。诚邀您围绕文艺作品、事件、现象等,发表有态度、有温度、有深度的评论意见。文章2000字以内为宜,表意清晰,形成完整内容。来稿一经采用,将支付相应稿酬。请留下联系方式。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投稿邮箱:wenyi@gmw.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