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贾力苈
近年来,众多电影经过改编后搬上舞台。这其中不仅有《十字街头》《永不消逝的电波》《肖申克的救赎》等中外经典电影作品,还有《完美陌生人》《看不见的客人》《消失的她》《爱情神话》等高口碑或引发热议的近年新作。从电影到舞台的改编,几乎涵盖了舞剧、音乐剧、话剧、新空间演艺等所有戏剧形式,有些作品还强调沉浸、互动体验,受到年轻观众的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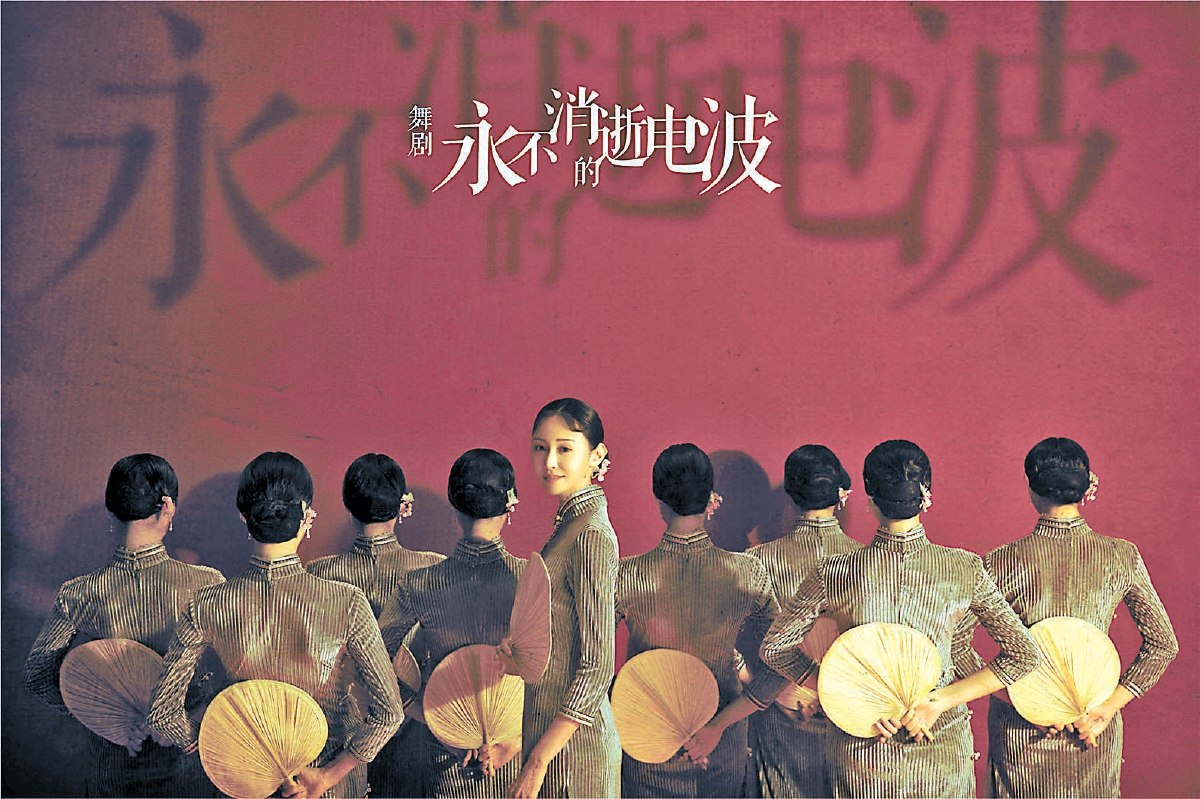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供图/上海歌舞团
戏剧与电影两门艺术在手法与内容层面的互动由来已久,这并非一个新话题。而当前舞台创作在题材选取、改编方式上呈现出新的特点,似乎正在开启一个电影为舞台艺术“输血”的新阶段。电影的技术优势与商业属性为戏剧带来了流量与审美新变,也为观众带来了新的观剧体验,而这些能否转化为戏剧发展的新动力?

话剧《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供图/国家大剧院
向电影借力并不简单
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无论中外,电影与戏剧的相互借鉴和改编,都与电影的历史一样久远。其中,将戏剧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创作路径更为常见和主流。这背后存在一定合理性:从时序上看,在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戏剧面前,电影显然算是新兴艺术形式,戏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为电影的题材、内容、结构提供了重要支撑。
相比之下,将电影改编为戏剧的做法就要少得多——虽然也有了《日落大道》《狮子王》《比利·艾略特》《雨中曲》等音乐剧佳作,《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千与千寻》等话剧新作,但从数量和影响力来看,由电影改编而成的戏剧经典依旧稀少。在理论研究领域,对这一改编方向的阐释也相对匮乏。
与戏剧相比,电影具有天然的技术优势,在时空场景切换、叙事角度转化及营造逼真效果等方面更具灵活性和创造力。将一部经过现场和市场检验的戏剧作品改编成电影,往往能实现叙事时空的拓展、角色数量与故事内容的扩充及视听效果的升级。而将电影改编为戏剧则面临更多的技术挑战:虽然二者都是视听艺术,但戏剧难以复刻电影镜头中的真实感、叙事的流畅度,创作者需要将剧情尽量控制在有限的场景中,同时需要将电影镜头里的真实感创造性转化为具有现场共时性的观剧体验。此外,虽然知名电影作品自带良好的受众基础,能为改编后的舞台作品引流,但观众对原作的好感和熟悉度也会拉高其对改编作品的期待值,增加改编难度。
将同为视听语言的电影改编为戏剧,要与电影形成区别,发挥戏剧语言的独特性,需要创作者突破原有银幕角色和故事在观众心中的固有印象,同时以戏剧形式对作品原有主题与精神进行富有创造性的阐释和传递,让观众感受到剧场这一媒介的独特魅力。若电影本身已改编自小说,那就会对创作者的跨媒介改编能力提出双重转化的要求。
创造独特的“戏剧瞬间”
近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伦敦西区原版话剧《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引发关注。这部作品改编自2012年李安执导的同名电影,实现了一次具有挑战性的跨媒介艺术转化。其主体情节是少年派遭遇海难后,与一只叫理查德·帕克的孟加拉虎共同在海上漂流的经历。电影中,电脑动画制作的老虎与少年派被困在船上的逼真场景,能让观众强烈共情少年的危险与艰难;但在舞台上显然不可能复制这样的时刻,于是创作者找到了让老虎在现场“呼吸”的方式:由演员操作老虎木偶,赋予老虎拟人化的语言与动作,让观众体验到剧场“艺术假定性”的魅力,进而理解故事中对人性的复杂隐喻和丰富的叙事层次。正是因此,该剧被评价为“创造了神奇的戏剧瞬间”。
所谓“戏剧瞬间”,指的是在演出过程中,跳出对视觉逼真度的机械复制,通过戏剧独有的假定性艺术手段,在特定时刻激活观众的想象力和情感共鸣,使其为之兴奋、为之动情。
电影与戏剧语言各有优势,电影长于技术与视听呈现,戏剧的核心是演员的台词与肢体表达。在电影院里,观众期待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与细节还原,而在剧场中,观众更愿意看到演员借助自己的身体和非常简单的道具,也许只是一条绳子、几个箱子、几把椅子,演绎出世间的万事万物。
近年来,中国戏剧人围绕创造这种独特的“戏剧瞬间”,进行了不少有意思的探索与尝试。有的作品通过切分舞台空间、交替叙事,实现原本需要镜头组接完成的叙事节奏;有的作品则对特写、远景、推拉等镜头语言进行创造性转化。去年黄盈导演了经典电影改编的话剧《乌鸦与麻雀》,电影原作讲述上海解放前夕,一座石库门老房里底层房客与官僚斗争的故事。舞台复刻了电影中的建筑,通过对空间的拆分和重组,让观众席与舞台形成类似电影观众与镜头之间的关系。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鹿鼎记》(2009年首演版),以移动的城墙道具模拟主角在紫禁城中奔跑的镜头拼接;在擒拿鳌拜的段落里,黑衣人托举演员从不同角度冲向观众席,引导观众想象韦小宝、康熙和鳌拜在打斗中的腾空、慢镜头和特写的画面效果。
黄盈还导演了另一部经典电影改编的话剧《十字街头》。电影原作有一条叙事线索,是男主角隔壁新搬来一位女房客,两人因为生活习惯差异产生矛盾,相互朝对方的房间扔纸团。原作通过多个镜头剪辑呈现这一场景,而舞台延续了“一墙之隔”的喜剧设计,两位演员背对观众分立两侧,面向同一侧象征墙板的方向扔纸团,在舞台上以类似电影剪辑的思维,让观众靠想象拼凑出完整的场景。
电影工业技术发展固然领先于各个艺术门类走在前沿,但舞台艺术凭借现场创造,能够为观众留下同样深刻的情感共鸣与记忆烙印。对于一些经典电影的改编,即使在叙事层面不做大的改动,也能通过舞台独有的手段制造亮点:龙马社改编的《肖申克的救赎》中,主角安迪手中的蝴蝶通过技术辅助飞向观众席时引发惊呼;英国国家剧院现场(NTLive)推出的改编自同名经典电影的舞台剧《奇爱博士》,将库布里克式的剪辑节奏进行转化,通过演员加速的台词、夸张的肢体,以及刻意制造角色反应与事件的不同步,以独特的喜剧表演节奏强化了原作的荒诞感和讽刺意味。
商业诱惑与美学创新博弈
电影与戏剧的相互改编,还涉及如何处理通俗与高雅艺术定位的问题。电影虽有商业片和艺术片的类型之分,但在现实中商业与艺术的界限是具有弹性的。将电影改编为舞台作品时,电影的商业属性不可避免地会对戏剧形成诱惑,产生影响。
成熟电影IP的商业诱惑不言而喻,较低的内容风险、数量可观的潜在观众群,都是创作者的底气。如何将兼具商业性与艺术性的电影佳作,改编为不失艺术性又能取得良好市场表现的舞台艺术作品,考验的是戏剧创作者对电影原作的解读能力。然而,若一味追逐IP、忽视戏剧本体,甚至为快速吸引目标受众而生硬复刻、堆砌原作精彩片段,甚至做出“媚粉”之举,牺牲的自然是作品质量。
商业与艺术博弈的背后,是流量与艺术本体的辩证关系。当下观众对改编形式与方法越发包容,他们最在意的并非改编是否忠实于原作,而是创作者是否用新的艺术语言表达原作精神,是否对原作精神进行了从当代视角出发的延伸、丰富甚至颠覆,从而衡量自己是否有必要在剧场里再体验一次这个故事。
虽然商业逻辑日益强势,但美学创新的意识依然不能忽略,尤其是对热门IP的改编。近年来,不仅是电影,越来越多的热播剧集也被搬上舞台。由于电视剧叙事篇幅长,可容纳的时空范围广,若在相对有限的舞台时空里过于追求还原尽可能多的剧情,满足观众对复现某个角色人设的期待,反而会让没看过原剧的路人观众陷入理解困境,将潜在的剧场观众拒之门外。
这种对商业逻辑的过度迎合,本质上是对舞台美学的忽视。反观这两年火出圈的越剧《新龙门客栈》,作为对经典武侠电影的跨界改编之作,其成功之道,正是以越剧独特的唱腔和表演(女小生传统),演绎观众在电影镜头里熟悉的武侠世界,同时采用环境式音乐剧的表现形式。这种创新不仅没有削弱电影IP的吸引力,反而通过美学革新拉近了经典与年轻观众的距离。
本土美学才是智慧锦囊
在数字技术时代,各种艺术门类的技术与语言更普遍、快速地相互影响,因此,我们更需审视戏剧艺术本体的魅力,在中国电影与戏剧的互动背后,看到丰富的文化与美学土壤。
蒙太奇是电影的标志性语言,其魅力在于,电影镜头剪辑通过间接、暗示的方式,引导观众理解剧情的发展。这种不以复刻现实为目的、强调含蓄的美学,其实广泛地存在于中国传统艺术之中。我们首先就会想到中国戏曲“一桌二椅”与程式动作所激发的丰富想象,以桨代舟、以鞭代马,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如果追溯中国本土电影与戏剧相互改编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电影自诞生伊始,便与中国戏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戏曲,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中国电影“借法”戏曲的起点,是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拍摄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段,它以接近于戏曲舞台纪录的形态,成为中国电影诞生的标志。中国电影在早期的主流称呼是“影戏”;戏曲不仅是早期中国电影拍摄的内容,二者的结合还催生出“戏曲电影”这一独特的民族电影类型。
早期中国电影创作多由戏剧人跨界参与,此后很长时间里,田汉、欧阳予倩、夏衍、洪深等创作者活跃于电影和戏剧两个领域。在中国电影与戏曲的本土交互中,戏曲不仅为电影提供了素材、注入独特的情感力量,更在创作原理与方法上提供了经验。同时,大量戏曲直接改编自国内外电影故事,如改编自1928年同名武侠神怪电影的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沪剧改编本土同名电影的《孤儿救祖记》,以及马师曾、薛觉先等人将美国电影改编成粤剧。
此外,中国戏剧人很早就开始借鉴电影技术,自1926年起在上海流行十余年的“连环戏”,如《凌波仙子》等,让演员在舞台演出时同步播放电影,以呈现难以现场表演的场景,解决戏剧叙事的时空局限和彼时电影无法发声等问题,让当时的观众耳目一新。
从“连环戏”到如今流行的沉浸式,都体现出在技术与艺术、商业与艺术的碰撞中,本土美学为拓宽舞台艺术边界和实现美学创新提供了经验与智慧。
摄像机“入侵”舞台之后
如今,讨论戏剧对电影的借鉴,已经不能局限在传统镜框式舞台的范畴里,新技术的叠加让二者的转化变得更加复杂。
近年来,舞台不单将电影的题材和内容“拿来”,还直接向电影技术与语言“取法”。2014年,英国导演凯蒂·米歇尔的《朱莉小姐》来华演出,将舞台打造成电影片场,通过严谨周密的设计,对舞台表演进行拍摄并实时生成、播放影像,创造出电影与戏剧表演的合成体。通过米歇尔的作品,中国本土戏剧创作者了解、接受了舞台引入摄像机、实时影像等方法和理念。自此开始,实时影像成为颇受中国戏剧创作者青睐的手法,如田沁鑫导演的新版《狂飙》、李建军导演的《世界旦夕之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悬疑三部曲”《深渊》《心迷宫》《生吞》等,均将屏幕作为重要的叙事媒介和层次,拓展舞台讲述故事的角度和空间。
一般来说,电影观众只能全程完全被动地跟随导演的镜头引导理解故事,电影镜头的景别角度、被拍摄人物和景观,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情感认同。而在剧场里,即使是传统的镜框式舞台,全程安静坐在座位上的剧场观众,也比电影观众更“主动”,因为他们可以自主选择看向舞台的哪个位置、哪个人物。何况如今摄像机、屏幕影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舞台上,沉浸式、移动式等多样的演出空间和新型观演关系层出不穷,这些都会让戏剧观众的视点交织。新技术越来越多,如何将这些技术用在向观众有效传递特定的情感与艺术效果上,而非单纯炫技,成为当下舞台语言创新的关键。
先进的技术固然能够营造出让观众信服的真实场景,进一步强化被动的沉浸感,但来到剧场的观众更希望看到演员如何当众完成“从无到有”的过程。观众能够随之调动视线捕捉细节,用想象填补场景的空白,从而实现对整个故事的建构。这样的观演体验,才是戏剧保持独特魅力的根基所在。
可以预见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必将推动电影在创造真实、营造奇观方面加速演进。将电影改编成戏剧,单纯追求热点IP或者探索如何复制真实,显然都非解题之道。面对求新求变且已见识过大量数字艺术的观众,戏剧若想保持不可替代性、找到创新发展的动力,就需要更辩证地审视电影与戏剧的关系,挖掘本土美学,总结百年前中国戏剧人、电影人的实践经验,于数字技术时代实现舞台艺术的主动出击,让戏剧艺术焕发新的活力。(贾力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