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王海峰
《去有风的旷野》(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是一部游记体散文集。这本书是一次“生态写作”之旅,是“去有风的旷野”寻找生态的踪迹。所谓生态,是指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状态。生态写作是对生态的书写,即将生态学原则与文学融合的一种现代性写作方式,它强调尊重自然与命运共同体,倡导环保与可持续发展。阿来在这本书中,以我“看梨花”而非“我看”梨花的方式,将生态作为文学的真正书写对象,给予呈现,给人理性的宁静、诗意的热忱之感。这种写作方式,不仅表达了阿来的生态观,而且呈现了一个悠久而伟大的生态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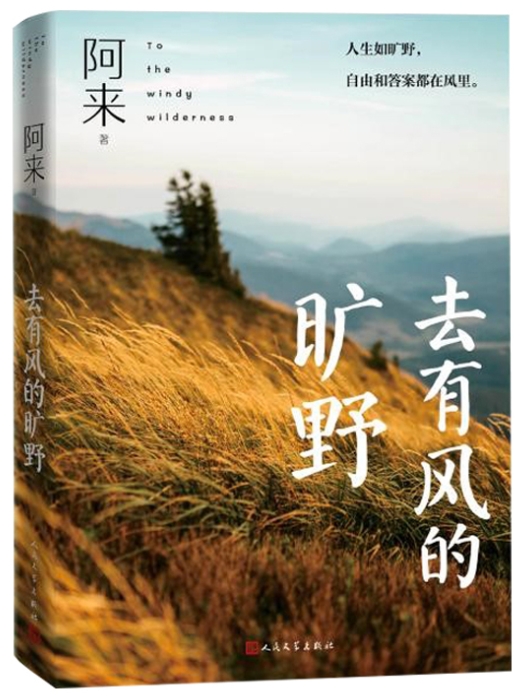
《去有风的旷野》由十篇游记集成,所游地域涉及“十二背后”、四姑娘山、“莫格德哇”、米仓山、“贡嘎日松贡布”“扎谿卡”、大凉山等十余处,所看景象涉及雪山、荒野、古道、云杉、杜鹃、沼泽、湖泊、岩洞、峡谷等。阿来经常徘徊在中国地理学家徐霞客与德国植物地理学家洪堡的历史踪迹之间,以自己的视角观看眼前的真实生态。他往往以静观的方式,直观地呈现自然之美:“在十月深秋,枯黄草地上的蓝,星星点点,簇簇团团。在阴天,这蓝是忧郁的;如果太阳出来,光线明亮,那时龙胆花的蓝和肋柱花的蓝就如蓝宝石一般闪闪发光。龙胆的蓝色花正在盛开,经霜后的线形叶已经变红了,经过霜的茎似乎变软了,匍匐在地,但仍把一只只钟形花朵斜举着,让它们倾斜着朝向天空,朝向光。它们的颜色是这世界最纯净的蓝,学名唤作蓝玉簪龙胆。钟形花的下半部,还间以黄色的脉线。肋柱花还直立着,在风中轻轻摇晃。”阿来以古典风格的文字,最大可能地还原他所寻找的生态踪迹,并在诗意与科学之间找到一种难得的平衡。
这种平衡要求作为自然“主宰者”形象的人的主体性退出,而仅仅以观看者或“自然之子”的身份,书写原始的生态世界。例如,阿来写道:“我想伸手抚摸一下柱头,但终究没有,我怕这一伸手,抹去的那点乳浆,就是几十年的时间。水蚀空石头,同时,水制造石头。旧的石头,变成新的石头。”阿来的观察视角,比瓦尔登湖畔的梭罗更轻盈,比书写自然的爱默生更客观。
作为生态写作者的阿来,既与自然保持科学的距离,又与自然进行诗性的融通。例如,阿来写道:“吃蔬菜让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吃肉觉得自己成了某种凶猛动物。吃饱了蘑菇,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棵树。”这种人与自然的融通,还体现在了阿来对于自然的观念及看法上。阿来虽然给出了植物学意义上关于草的定义,以及许多名字,但是,他更喜欢中国古籍中的命名:“生曰草。”“人的历史湮灭无迹处,草生生不息。”阿来寻找到了渺小的草在中国生态观念中的本真含义。命名决定着人对生态的观念。当马的主人将马称作“牲口”时,阿来坚持说它是“马”,不是牲口。他的生态观在给生物命名的那一刻,变得生动、博大。阿来仔细书写每一种植物、动物,仿佛在用名字诠释生态的本真,指认每一种生物无可替代的意义与价值。
在阿来的生态观里,既有对生态的整体观看,也有对弱小生物的额外关照。阿来写道:“梦境中,藏野驴和普氏原羚在啃食那些花丛周围稀疏的青草。藏野驴和羚羊种群的增加被视为三江源地区生态转好的标志,我却担心那些稀疏到不能覆盖沙土地面的弱小青草。在如此靠近生命禁区的高度上,少数的、孤寂的生命,在如此广大的地域内的存在,竟具有某种符咒般的魔力。”“睡不踏实,总是恍惚看见荒原上有限的那几种开花植物。”阿来对野草踪迹的寻找,好像小王子对玫瑰的挂念,总让人在浩大的自然之旅和生态历史中,感到某种真切的柔情。在阿来看来,自然四时皆有其美景,生态万象都独具蕴意。自然生态之境,并无大小高低之别,只是人们的主观划分罢了。阿来的生态写作,正是要打破这种既有的生态观念,继而以生态写作的方式,重建一个观看生态中国的整体性视野。
阿来的生态写作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的,旨在持续培养一种观看自然的新感受力;不仅指涉空间,而且关注绵延又共生的时间。当谈及文旅融合这一问题时,阿来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为地方文化旅游产业提供了一个生态学视角,倡导“对公众进行自然知识普及和自然生态教育”,让人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地质、山脉、水文、植物、动物。他试图通过生态写作除去所有人工的粉饰,把自然的本真与历史还给读者,还给时间,似乎要让自然重新孕育人、发展人、完善人。阿来感慨道:“地球在其演化史上,造就了不同的自然奇观……但它们仍属于同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生活的不同世界原本属于同一个世界。”阿来的笔下将时间与命运相连。时间如水,流经四面八方,雕刻出一幅幅生态地图:时间、地理、人文与生命经验的交汇和发展。
在《去有风的旷野》中,不仅能寻到中国历史、文学史、文化史的踪迹,也能寻到利用科学开发自然、哺育人类的思路。阿来对杜鹃、红叶、荇菜、古道、蜀地山川等自然与人文生态的书写,不可避免地引发他对中国历史、地理、古典诗文的美学与生态学的思考。阿来并未将古典与现代对立,而是更多地强调,现代化不应抹掉自然的本色。古典与现代的流动本性也须遵循生态规律,因为它们在自然的怀抱里,像黑格尔所言的花朵和果实一样,是有机统一的。它们共同构筑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与此相对,便是阿来对“淘金”、盗墓、捕猎、非法采矿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批判。更进一步,阿来提倡用科学的、生态的方法与途径实现乡村振兴。这种科学的、生态的路径,需要科学家和生态学家了解和热爱一片土地,发现这片土地的生命潜力,找到适合土地滋养又能反哺土地的经济作物。在阿来的生态写作观念中,人对现代性的寻求,恰恰需要借助自然之力,因为人的历史孕育在自然的历史中。
从水泽到大河,从旷野到心灵,阿来的文字无不灌注着一种生态写作的理想:过一种幸福的生态生活,建设一个美丽的生态中国。这部散文集不止于呈现自然文学对生命细微的书写姿态,也修正了既往游记体散文的主体偏向。在《蔷薇科的两个春天》文末,阿来关注到游记体散文的一个危机:“只看见规定的意义,却不见对象的呈现”,即写作主体对生态的“刻板印象”,掩盖了生态的本真。所以,阿来笔下的生态,有别于一般游记、自然文学及报告文学中的生态。他不仅看到了生态与人文的关系,还看到了生态演化的历史痕迹、植物学意义上的生态奇观,以及自然时空里那种“伟大的寂静与洪荒”之力。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创意写作学博士,中国写作学会理事)
